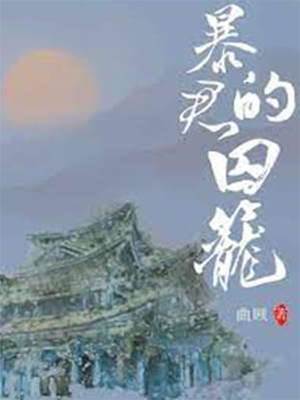《玲瓏雪》 第 72 章
第 72 章
“誰?”
“赤冶劍, 顧家三郎!”
“今兒這頓飯賺大發了。”
“可不是,赤冶劍那可是神兵的祖師爺。”
......
一時間,華樓二樓了一鍋粥。
期間, 樓梯間不斷地有急切腳步聲傳來, 明顯是外面的人聽到異往樓上趕,生怕錯過好戲。
那被削傷了耳朵的錦袍公子, 了把耳朵, 鮮沾了他的指腹,他的目驟然冷了下來。
他邊公子哥模樣的人也圍了過來, 有些細致探查他的傷口, 有人怒目朝向不知何時出現在此的顧紹卿,
“原來是顧家那個有爹生沒娘養的三爺吶, 今兒一見, 果然是毫無教養。”
說話的須臾功夫, 赤冶劍在空中打了轉兒又回到了顧紹卿的手中, 唰的一聲, 消失了。
此舉讓周圍看客嘖嘖稱奇,這顧家三郎好生有趣, 說話輕佻冒犯了郡主他下狠手, 罵他自己,他把劍給收了。
顧紹卿對旁人思緒一無所知, 他盯著這幾位錦袍公子,眼神冰冷, 約著悲憫,仿佛在看死人, “衆目睽睽之下,對一子施以輕佻言語, 你們可真有教養。”
幾位錦袍公子哥頓時失了聲音,不過也就片刻,便又有人朝著顧紹卿囂,“關你何事?”
顧紹卿:“當然關我事。那我徒弟,也是當朝郡主。你方才所說的那句,夠治你個大不敬了。”
“擱這等著吧,李督捕很快到。”
說完,他扭頭看向後,對著一衆湊熱鬧的,“誰去承前州府報個信?民衆主揭發惡人惡事,若查證屬實,視案件大小,酌給與獎勵。”
鄉裏鄉親立馬就聽明白了他話中的含義,這是把賺錢的機會給了他們這些街坊,不然以顧家三郎那輕功,來去也就片刻功夫。
Advertisement
“三哥,我去我去,我跑得快。” 一位半大不小的年忽然大聲嚷嚷,嚷完拔就跑,生怕機會給人搶走了一般。
他那一聲“三哥”仿佛在糖漿裏滾過一遭,黏黏糊糊的。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顧家三郎也了西地人盡皆知的人,并且下意識篤定只要不犯事兒就用不著怕他懼他、甚至可以依賴。
顧紹卿凝著人群,角若有似無地了下。隨後扭過頭,徑直朝著陳夕苑而去。同那位被削了耳尖兒的錦袍公子錯而過時,那人終于消化完顧紹卿的話,面驚慌。
他趕忙轉過,朝著陳夕苑行禮,之後連扇了自己幾耳,落足了力,扇完,那張俊臉紅得發燙,“嘉陵有眼不識泰山,還郡主恕罪。”
此人名喚郝嘉陵,來自承前州的又一臨州嘉陵州。家裏頗有些底蘊,四代以,還出過一個州主。平日裏持著顯赫家世,在州橫行霸道,也沒調戲漂亮姑娘,今兒種種不過是習慣使然,哪知踢到了塊鐵板,還是最的那種。
陳夕苑最是不喜這種對子自詡風流倜儻對子口花花的公子哥了,而且顧紹卿已經有了主意,再怎麽,也不會當著這麽多人駁他的面子,這些人也不配,“這罪本郡主是恕不了了,有話,去州府和段州主說吧。”
“嘉陵公子可要好好的說,畢竟這麽多人都瞧見了,容不得你抵賴。”
說完,撤回目。
沒多時,華樓掌櫃終于出了人群,他心裏連罵了好些聲晦氣才勉強住了罵人的沖。向顧紹卿和陳夕苑致歉後,忙著將這幾位往一樓趕。
路人街坊見沒戲看了,紛紛離去。
半盞茶的功夫後,陳夕苑一行人離開了華樓,孫驍獨自上了馬車。
Advertisement
陳夕苑隨著顧紹卿慢步閑逛,看斑駁街道憑聲尋鳥,極是尋常,卻已足夠愜意。
走了一段,人兒憋不住話了,開始問東問西。一如所想,袁知弗昨夜經歷的種種都是顧紹卿和蕭弘玄的手筆,鬧到大半夜也不覺得困,四更天,又出發去了七寶村。
“幹得好。” 陳夕苑由衷地誇贊道,很厭惡什麽人,這袁知弗絕對是其中之一。
顧紹卿沒吱聲,但觀其狀態,能清楚辯知他是極為松弛的狀態。他信任邊的人,卸下了所有的防備。
陳夕苑對這種境況太過悉了,毫不以為意。兀自說著問著,直到某個瞬間,有個念頭毫無鋪墊地掠過的意識海,隨即停下了腳步,定定地睨著顧紹卿。
顧紹卿莫名其妙。
等了會兒,還是這般。
“看什麽?”
陳夕苑仿佛到了驚擾,長而薄的睫羽重重地了下,下一個頃刻,以一貫的和語調,“哥哥,碧華閣的人漂亮嗎?”
顧紹卿:“......”
這便是傳說中的送命題吧?
還沒緩過神呢,人兒又開口催促了,“哥哥,你為什麽不回答?”
很明顯的,不掰扯清楚是不會善罷甘休的。陳氏大倔種,可不是他吹出來的。
如此,顧紹卿若不想今晚被煩死便只能答,“不清楚。”
陳夕苑:“什麽不清楚。”
顧紹卿:“......我沒仔細看,不清楚們樣貌如何。”
陳夕苑:“不可能,那綠樺是西地聞名的大人,你的那陣‘風’都掃到了,了?就這還能看不清長什麽樣兒?”
起初,陳夕苑只是想逗他鬧他,期待看到他變臉。不想說著說著,竟真的酸了起來。
不喜歡顧紹卿像抱那般抱別人。
Advertisement
這些想法湧出時,小臉的線條趨于繃,或許都不自覺,沒能做出任何僞裝。
顧紹卿看在眼裏,一種類似驚喜的激昂緒自心底湧出。
陳夕苑在吃味嗎?
喜歡他,并不僅僅是時間堆出來的慣依賴。
當意識到是真的在意,正在難過忐忑,他不正,萬般認真地解釋道,“那風確實出自我手,但我沒到,也沒看。”
“我不信。”
至此,和胡攪蠻纏差不多了,顧紹卿一方面覺得荒唐,一方面又覺得可得不能行。心房間的歡喜也越發的濃馥,是他從未會過的陌生覺。
“不信是不是?”
“嗯。”
“那我現在證明給你看。”
“怎麽......”
後續的話沒能說完,因為顧紹卿忽然有了靜,他先是疾步往後退了一程,然後右臂一揮,磅礴而和的沖擊力頓時將人兒裹挾,迫著往後退。
而他,本沒到。
“信不信了?”
“.......”
明兒就開始抄寫田氏氣功。
......
顧紹卿回到小院,一如從前,在院的井旁拎冷水洗漱。
半晌折騰,他躺到了床上。
這段忙得夠嗆,昨夜又沒怎麽睡,眼下有時間,他該抓時間補眠才對。但他嘗試過了,本睡不著。
一闔上眼,眼前就會浮現出陳夕苑冷著杏眸嗔他的樣子,那時候的分明是一冷豔,可他莫名地覺得可......
思緒如小爐滾水,細的翻滾著。
他沉浸不知時間過,忽而有細微聲響自前院傳來。
顧紹卿起,慢步踱到院。果不其然,有一只黑鴿停在t了老樹枝椏上。它黑得很純正,若不是它腳上綁著東西并非黑,它幾乎同這濃墨的夜融為一。
顧紹卿走近了些,取了信。黑鴿輕而短促的咕了兩聲,震翅飛走了。
顧紹卿回屋,燃了燈。展信細閱,是明月樓主的信,簡潔又明了。
七日,一手錢一手東西。
浩瀚飲食在恢複,也開始願意翻閱醫書,一切向好,勿念。
顧紹卿的角若有似無的彎起。
等他拿到了珩公子手中的那幅畫,近期種種,也算完收尾了。
翌日,顧紹卿又是早早地去了七寶村,甚至比之前幾次還要早。這兩三日,他必須趕完最後那批石刀。
之後,他得跑趟闋歌國。若順利,他能趕回來陪陳夕苑吃“春日宴”。
在西地,每逢四月初,新綠一寸寸漫開時,整座城無論是世家還是富商大賈,都會設宴款待西地鄉民,略帶薄禮,就能地吃上一頓,經歷這西地獨有的春日喧熱。
抵達,開幹。
饒是如蜚老人這茅草屋的每一塊磚板都是特制的,那刺骨的聲兒還是傳了些去屋,壞了如蜚老人的睡眠。
開天窗,辯天。
“......” 又是四更天。
這破小孩是不用睡覺嗎?
吵醒了,再睡就難了。如蜚幹脆起,收拾妥帖,推門朝著顧紹卿而來。
“這回又是要去幹什麽?” 語氣不見好,但其實心裏沒什麽怨念,反而有些心疼他。別家若是有這麽個孩子,樣貌俊秀天縱英才,不知道多著重。哪兒可能像現在這般,盡冷待,大事小事都要靠自己。
經過這段時日的相,顧紹卿早就習慣了老者的刀子豆腐心,毫沒將他的冷喝放在心上,“有點事要出去兩三天。”
“不過您放心,該幹的活我一定會幹完。”
這一點,如蜚老人倒是不擔心。顧紹卿什麽子他還是知道的,他要麽不答應,答應了就一定會竭盡全力將事兒幹好。退一萬步講,就算顧紹卿不想幹撂挑子了,他還能去找姚寒江來磨。徒弟的債,師父來抵,沒病。
相比之下,他更好奇他要去幹什麽。
兩三日,以顧紹卿現在的速度,這不是要去異國就是去帝都吧?
顧紹卿默了默,“先生可了解珩公子?”
如蜚老人眼睛微瞇,“昭珩?”
“你要去找他?”
顧紹卿:“對,明月樓的差事。昭珩此人聲名在外,但見過他面的人極。”
“他常年在闋歌,同瀧若早就失去了牽連,這次又為何派人來狙殺溫浩瀚?”
“日前,尹監州從甘棠帶了個乞丐回來,他可證滅溫家一門的殺手來自北地,同昭珩并不是一路人。”
“滅門為那紙藥方,那昭珩他想要什麽?好巧不巧,有人在這個節骨眼上花巨資請明月樓去昭珩盜一張畫......”
顧紹卿細致地說出了自己的想法,一方面回應了如蜚老人,另一方面是在複盤。他總覺得溫家滅門一案表面上看著要結束了,其實并沒有,而這昭珩很可能是其中關鍵。
如蜚老人聽完,似忽然想到了什麽,“你跟我來。”
顧紹卿:“做甚?”
如蜚老人眉頭蹙起,“跟著來就是,哪兒那麽多廢話。”
話畢,自個兒先進屋了。
顧紹卿這才扔下了手中打磨到一半的石刀,跟了上去。
“第四層第三本,第八層第九本, 第十二層......”
進了屋,如蜚面向一面高聳書牆,報一數,指尖指向一。
“這四本書拿下來。”
有顧紹卿在,搭梯都省了,快又安全。如蜚老人使喚得也是自然而然,沒有半點負疚。
顧紹卿雖不明所以,還是幫他取了書。幾番起起落落,取齊,兩個人倚著茶塌而坐。
如蜚老人最先翻開的是,《乾坤輿圖》。這書都不知是誰編撰又是幾時出的,反正顧紹卿讀過那麽多的書,連這書的名兒都沒聽過。
如蜚循著目錄查找,翻到了【極北】的頁面,隨後輕輕拽拉,廣袤北地的輿圖頓時映兩人眼底。書太過老舊,鋪開的過程中,有細微煙塵氤氳而出。但這一老一小,無人在意。
細致梭巡後,如蜚老人的指尖落在輿圖一點,以這個點為起點,慢慢掠過,勾勒出一條起起伏伏的線。
“知道這裏是哪裏嗎?”
顧紹卿答道,“瀧若和安槐龍元兩國的邊界線,界碑之所在。”
如蜚老人眼底有贊賞氤氳而出,“沒錯,你小子還怪有見識的。”
說完,他放下了輿圖,換了另外一本書。
《龍脈寶》
這是一本有關風水寶地的書。他索著翻到了其中一頁,他明顯認真閱讀過,一些句子被特別標注出來。其中一句,輕易地拽住了顧紹卿的目,
猜你喜歡
-
完結8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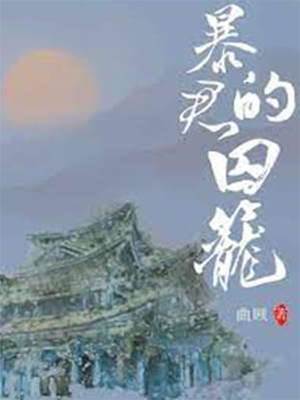
暴君的囚籠
鎮國公家的幼女江知宜自幼體弱,一朝病重,眼看就要香消玉殞。有云遊的和尚登門拜訪,斷言其命格虛弱,若能嫁得像上將軍那樣殺氣重、陽氣足的夫婿,或許還能保住性命。鎮國公為救愛女、四處奔波,終於與將軍府交換喜帖,好事將成。然而變故突生。當夜,算命的和尚被拔舌懸於樑上,上將軍突然被派往塞外,而氣咽聲絲的江知宜,則由一頂轎攆抬進了皇宮。她被困於榻上一角,陰鷙狠絕的帝王俯身而下,伸手握住她的後頸,逼她伏在自己肩頭,貼耳相問,“試問這天下,還有比朕殺氣重、陽氣足的人?”#他有一座雕樑畫棟的宮殿,裡面住著位玉軟花柔的美人,他打算將殿門永遠緊鎖,直到她心甘情願為他彎頸# 【高亮】 1.架空、雙潔、HE 2.皇帝強取豪奪,愛是真的,狗也是真的,瘋批一個,介意慎入! 3.非純甜文,大致過程是虐女主(身)→帶玻璃渣的糖→虐男主(身+心)→真正的甜
27.4萬字8 28939 -
完結637 章

腹黑王妃要改嫁
"靠山山倒,靠水水幹,靠天靠地考父母靠男人,都不如靠自己來的安全實在。杜錦瑟自認自己不算聰明,不過還是勉強可以自力更生的。只是老天何其不公,讓她這樣的的小女子在皇權傾軋中求生存,累覺不愛。埋怨有用,她就坐在那裏埋怨好了。可惜埋怨解決不了問題。看她如何周旋于各懷鬼胎的皇子們的中間,玩轉皇權,蔑視皇權,把看不起她的通通踩到腳下。"
96.2萬字8 22787 -
完結144 章

求魔
我在幽冥最骯髒的地牢深處,遇見了世上千萬年來最至惡的魔。 他是三界最隱秘的不可言說,是神仙們的夢魘,是早被曆史埋葬了的酆都惡鬼萬惡之首。 他死去萬年,又從毗羅地獄中歸來。 那天,他救下我。 從此我多了一個主人。 我追隨他,服從他,做他的提線木偶。 而他給予我一切——他的血替我重塑經脈,脫胎換骨,代價是我必須靠他的血活著。 在他的庇護下,我進入第一仙門,進境飛速,成為同輩裏最驚才絕豔的第一天才。 他要我拜掌門為師,我便拜;他要我偷取至寶,我便偷;他要我競奪道門頭魁,我便爭…… 後來,他要我設計勾引,嫁給掌門之子。 我知道,他想要從根上毀了這座仙門。下命令時他懶洋洋靠在月下的青石上,雪白的衣袍半敞,長垂的發絲間笑意冷漠又惡意。 這仙宗道門修者萬千,世間一切不過螻蟻,是他玩弄於股掌的一個小遊戲。 而我也隻是螻蟻中可以被他利用的那個。 我都知道。 但我不在意。 我嫁。 喜袍紅燭,人間盛妝千裏。 我學凡俗女子的模樣,作一副羞悅相,坐在婚房喜床上等我的夫君。 等了一夜。 沒等到。 天將明時,終於有人推開了窗。 他穿著被染得通紅的雪白袍,提著長劍,血從他來路拖著衣襟淌了一地,身後漫山遍野的血色。 他用滴血的劍尖挑下我的紅蓋頭。 冰冷的劍鋒吻在我喉前。 我抬頭,看見一雙隻餘下黑瞳的漆目。 那是世間頭一回,魔淌下了兩行血色的清淚。 他啞著聲問她。 “…你怎麼敢。” 【尾記】 魔是個奇怪的東西。 他要世人跪地俯首順從。 偏求她違逆。 *正文第三人稱 *成長型女主(心性修為雙成長,開篇弱小逐卷成長,想一上來就看冷血無情大殺四方建議直接繞道,你好我也好) *反向成長型男主(?) *微群像 【男女主he】,副cp與其他配角不作保 內容標簽: 前世今生 天作之合 仙俠修真 主角:時琉(封十六),酆(fēng)業(封鄴) 一句話簡介:我偏要,魔來求我。 立意:善惡應有報,天理當昭昭。
40.8萬字8 171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