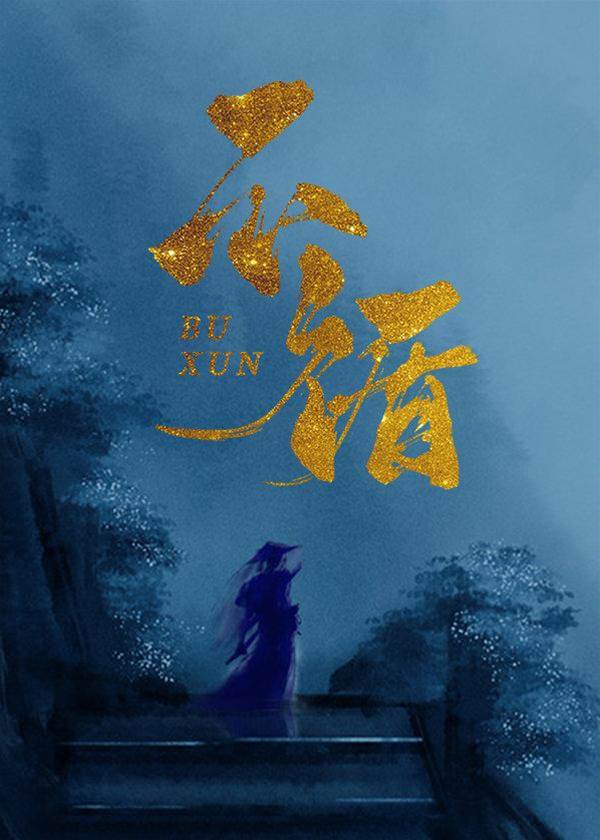《掩嬌啼》 第42章 自欺欺人
第42章nbsp;nbsp;自欺欺人
明月清夜, 那一抹突如其來的月華漸漸化作溪水,緩慢地淌狹窄的偏殿之中。
一切都似水靜謐,只聽見與低低的嗚咽疊。
不知多久過去, 連嗚咽聲都消失不見了。
越明珠大腦一片空白。直到被裴晏遲松開,大口著氣, 好久之後, 神智才重新回歸清明。
剛剛那一個又一個的片段全都在腦海中掠過,回到最初, 說了一件跟裴晏遲小時候的事。
然後就演變了現在的局面。
……上好疼。
這是越明珠的第一個真真切切的。
舌尖也麻麻的。
方才被吻得發懵, 所有都被強勢掠奪得一幹二淨。
如今緩緩回過神,若有若無的麻疼全都如針一樣紮來。
越明珠覺自己經歷了一場不輕的|。
囁嚅著, 聲音分外可憐:“好像也過敏了……”
頭頂上響起平靜的糾正聲:“我親的。”
越明珠小小的臉皺在一起,忍不住接話抱怨:“被你親得好疼。”
仔細著從上傳來詭異的溫熱, 又慢吞吞補充了一句:“還有一點點點。”
“我可不可以藥?”
裴晏遲慢條斯理地平剛剛被弄的袍褶皺,借著月看向那潤飽滿的雙。
破皮了, 的確有點狼狽。
他收回目, 道:“沒用。”
越明珠:“那怎麽辦?”
出手指想了瓣,結果正好到破皮的地方,當即就嘶了一聲。
盡管一早就知道裴晏遲平日如何人聞風喪膽, 但私底下相時見過他不為人知的另一面, 以至于越明珠快忘記了這件事。
如今才後知後覺地記起來, 原來裴晏遲在面前也會這麽兇。
Advertisement
原本還在後悔好像說了不該說的話讓他不高興了,現在倒好, 被欺負了一番之後, 越明珠突然多了幾分理直氣壯。
“為什麽要咬我, ”睫一扇,小聲地控訴, “有這麽生氣嗎?”
裴晏遲平靜地回答:“現在沒有了。”
他比還要理直氣壯。
越明珠長長地噢了一聲,終于理解了現在的況:“你把怒火都發洩在我的上。”
這話實在太有暗示的意味,裴晏遲頓了一下,才問:“話本裏看的?”
越明珠驚訝地睜大眼:“你怎麽知道?”
很顯然就不是這顆純潔的腦袋能想出來的東西,裴晏遲沒有回答,轉而提醒:“你的襟剛剛了。”
越明珠低下頭,才發現襟不知道什麽時候已經松垮得不這樣。還好前那些不爭氣的在這一刻終于發揮了作用,撐住了布料,才沒有讓的襟繼續往下掉落。
拿過衾被遮住,面一點窘迫:“你就當沒看見。”
裴晏遲嗯了一聲。
其實他剛剛一直都當沒看見,只是再不提醒,就要徹底遮不住了。
氣氛又就此安靜了下來。
越明珠忍不住去看裴晏遲。男人後是黯淡昏黃的燭,側披著清冷如銀的月。
月。
突然想起迷糊中聽見那道奇怪的聲音,跟月一起闖了進來。
“子淮哥哥,剛剛你有聽到有人在我嗎?”
裴晏遲:“沒有。”
“真的嗎?”
接連兩聲,越明珠實在覺得實在不像是幻覺,“我怎麽覺好像有人來了?”
裴晏遲:“我沒聽到。”
越明珠指了指那半掩的窗戶:“那窗戶為什麽會開了?”
裴晏遲:“被風吹開的。”
越明珠將信將疑地眨了眨杏眼,問了第二遍:“……真的嗎?”
Advertisement
裴晏遲反問:“難道你不信我?”
越明珠當然信他,見狀不免重新開始懷疑自己,喃喃自語:“那我是被鬼上了嗎,我聽到一個很悉很悉的聲音在我名字……”
“你聽錯了。”
裴晏遲驀地打斷。
他的語氣又比剛剛不好了那麽一點。
見裴晏遲態度篤定至此,越明珠只好不再糾結這件事。
但還惦記著那沒關嚴實的窗戶,催促著裴晏遲:“子淮哥哥,你去把窗關上吧,等會兒被外邊的人看見就不好了。”
裴晏遲起,卻沒有走到窗邊,而是在桌前停下,倒了杯已經完全冷掉的茶水。
飲下之後,他才迎上越明珠膽戰心驚的目:“外邊沒有人。”
都當他是來接人的,一見到他就麻利地全退下了。
越明珠的心卻沒放下來,頓覺不妙:“那我今晚要一個人睡在這個地方嗎?”
裴晏遲瞥回來一眼:“你不回去?”
越明珠抱起被子,將下擱在隆起的衾被上,有些惆悵:“子淮哥哥,你是不知道……”
這個地方是為了方便隨便找的,呆起來當然不舒服,四周除了竹林就是荒郊野嶺。
方才困得不行才能瞇一會兒,但如今清醒了許多,也不知道要輾轉多久才能睡下去。
但是最初那大夫給把脈診出過敏,而後的過敏之癥遲遲不消退,大夫後面多次把脈,又無意間提了一句,可能是別的會傳染的病癥。
這可把準備來假惺惺探的貴嚇得不輕,一個二個都找借口離開了。
方太醫雖然說了只是被人下了藥,可真相尚且還未傳出去,這一晚上恐怕已經起了好多種說法。
怕今晚回去,會給住在隔壁的于清雙添麻煩。
裴晏遲:“給你下的藥,不應該是給你添了麻煩。”
Advertisement
越明珠一愣。
裴晏遲沒有同過多解釋。
事實并不難想通。越明珠什麽心思都掛在臉上,被于清雙發現知道了們的是很正常的事。
這種不流的手段,只有急于報複又年紀太輕的千金小姐想得出來。
“先送你回去,”他道,“明日再理的事。”
越明珠還沉浸在被于清雙下了藥的震驚之中,良久之後才反應過來,裴晏遲還在等的回答。
急忙應了一聲,剛想要下榻,手放下衾被,恰巧一陣涼風吹來,出的地方被吹得陣陣發寒。
越明珠這才想起來不妥。
這裳換得草率,實在不好出現在除了酣睡之外的任何時候。
越明珠瞥了瞥一旁掛著的換下來的,和旁邊低矮但尚且能遮的屏風,心中頓時有了主意:“子淮哥哥,我想先換件裳。”
雖然折騰了一下午已經疲力盡,恨不得就此躺回自己的小床眠,但是這種事馬虎不得。
裴晏遲沒意見,應言離開。然而剛走到門口,他又聽見越明珠喊他過去。
踱步回到屏風,後面傳來越明珠弱弱的哀求:“蠟燭太遠了,我在這兒看不清楚,可不可以幫我舉過來一點?”
自知這種要求有點麻煩人,說完又道:“不可以就算了。”
越明珠忐忑地等了等,竟然真的等到了一抹靠近的亮。
被系得七八糟的束帶在微下重見天日,一一解開,慢吞吞換回了之前合的裳。
哪怕是夏日,子的裳穿也十分繁瑣,尤其是越明珠手更慢。
裴晏遲覺得應該早點提醒,這屏風上糊的是宣紙。
非常非常薄。
被一照,站在前邊就能看清楚後面影影綽綽的廓,高低錯落都映得清晰。
一邊換裳,一邊還在檢查上有沒有疹子的殘痕,若無骨的手流連在手臂腰側。
還能看清越明珠穿上時猶豫片刻,用一只手將那片綿攏住,試圖系一點,結果被勒得差點不過氣,接著整個偏殿都能聽見急促的呼吸聲。起伏得呼之出,甚至能看見最上面還有一尖尖的像裳褶皺般的東西。
裴晏遲想,平時的心也許還小了一號。
越明珠正手忙腳,又聽見裴晏遲問:“還沒穿好?”
“馬上!”
也意識到自己作有點太磨蹭了,只好放棄那些細枝末節的東西,快速將裳穿戴整齊。
一轉眼,越明珠就從屏風後閃了出來。
拿過等會兒要的藥膏揣進袖裏,挪到裴晏遲邊,不好意思地道:“我們走吧。”
坐上馬車時,天已經徹底暗了,萬籟俱寂,一路上只聽見夏夜知了的鳴。
馬車緩緩行駛,越明珠看著對面裴晏遲毫無表的臉龐,突然道:“子淮哥哥,按話本裏面的節,這種時候都是讓我去你的房裏呆一夜的。”
挲扳指的作停了一下。
裴晏遲擡起眸子。
這種話跟邀請毫無區別,他著實好奇,越明珠到底從那些三流讀裏看到了多離奇的東西。
不過,若今日驚,這個提議的確未嘗不——
視線落在越明珠臉上,尚未開口應下,只見又抿起瓣:“但我最討厭那種|下|流的人了,還是子淮哥哥比較好。”
裴晏遲:“……”
車廂安靜了片刻,才聽見他平淡的聲線:“以後說那些從話本裏學來的詞。”
…………
越明珠本來就是貴間名不經傳的存在,那日意外雖然鬧出來點靜,但很快被人當一個普普通通的曲拋之腦後。
何良嫻從下人口中得知那日裴晏遲去探了越明珠,震驚之餘,下一切都明了了。
識趣地沒再打探越明珠後來的事,生怕一不小心就打探到越姑娘又進出了兒子的廂房,只能被迫裝聾作啞。
除此之外,更需要何良嫻心的是這幾日都夜不歸宿的裴驚策。
裴績可不會像那般好說話,回來得知況後,不由分說地就讓人把裴驚策拎到了跟前。
大抵是早已經習慣了面對滿臉慍的裴太傅,裴驚策靠在門邊不進來,站也沒個沒站相,雙手抱臂,垂著眼睛,看起來完全沒有在聽人訓話的自覺。
他眼睛底下有淡淡烏青,比平時多了幾分翳。
裴晏遲一進來,就聽見裴太傅冷冷斥他:“這行宮就這麽大,你鬼混的那些東西以為別人不知道嗎——”
一見到裴晏遲來,想起來還有正事,裴績只得按捺下話頭。
他的手摁在膝上,靜默片刻,才調整好神,用公事公辦的語氣問:“李大人那邊理好了?”
裴晏遲:“全部完備。”
他跟裴績各自兼重任,平時來往大多都是因為公事。
加之兩人都格偏淡,用何良嫻的話來講是老木頭跟小木頭,因而哪怕難得一見,也有為父子敘舊的時候。
裴晏遲隨即言簡意賅地道明來意:“方才見過陛下,他讓我把這件印信順路給爹。”
他擡手,莊河立即將印信呈上。
此要,遞到他手裏的意義非同小可,裴績神一正,思忖幾許後沒有多言,謹慎地頷首:“我知道了。”
聊起政事,廳堂明顯比剛剛安靜了許多。
原本只有裴績跟裴晏遲的聲音,直到裴驚策莫名嗤笑一聲。
他藏都懶得藏,那一下清晰地落在在場所有人耳中。
場面驟滯,裴績轉頭看向他,語調微沉地警告:“裴驚策,你整日廝混的賬,我還沒給你一一算過。”
“跟我算做什麽,”裴驚策毫不客氣地反相譏,他用詞一點都不知道收斂,難聽得格外刺耳:“太傅大人還是先問問你最爭氣的大兒子私下都怎麽宿娼狎的吧。”
話音落下,裴驚策也懶得管衆人的反應,直接轉離開。
裴績見慣了場面,沒被輕易激怒失態,坐著不,沉聲吩咐人去攔。
等人去了,他才擡頭看向裴晏遲。
面對父親眼中淡淡的審視,裴晏遲倒顯得無比平靜:“兒子先告退了。”
“……嗯。”
裴績沒多說什麽,何良嫻卻忍不住跑出去追上了裴晏遲。
將他拉到一邊,又低又急地問:“驚策是不是誤會什麽了?”
雖說裴晏遲已經幹出了白日宣|這種荒唐事,但也不至于有眠花宿柳的癖好啊!
該不會是裴驚策把越姑娘當什麽不正經的人了吧?
裴晏遲心如明鏡,沒有多說,只簡單地應了幾聲,安好何良嫻。
等他理完這一切走到門口時,裴驚策還被人攔著。
裴驚策奪了那人的棒,架在人脖子上不耐煩地喊了聲滾開,但其他圍著的人奉了命令,無論如何都著頭皮不讓,一時只得僵持在原地。
裴驚策眼中的不耐愈發濃郁,等餘瞥見裴晏遲從旁路過,他的表就顯然更差了。
裴晏遲難得沒直接離開,倏忽站定在一旁。
他看著旁邊停留的麻雀,不鹹不淡地開口:“律法中偶語者棄市,妄言者無類,二弟還是早日學會謹言慎行為好。”
很顯然,他是故意再度挑起這個話柄的。
裴驚策手攥長,頓了一頓,忽而冷嘲道:“是不是真的,你不應該比我更有數?”
“我還以為你應該看得很清楚。”
裴驚策這幾日又跟那群狐朋狗友廝混在一起,還讓薛家的大爺替他找來長得像越明珠的揚州瘦馬確認。
這些事,暗衛早就跟裴晏遲說過了。
裴晏遲著他倏忽繃的下頜,語氣甚至比往常平和些,不疾不徐地開口:“我對你自欺欺人的本領實在嘆為觀止。”
猜你喜歡
-
完結1674 章

彪悍農家妻:王爺,種田吧!
一次意外,蘇心妍穿越到了古代。爹不疼,奶不愛,家里一貧如洗,還有各種極品親戚上門找茬。幸好她有空間在手,種果樹,做美食,手撕白蓮,腳踢綠茶,發家致富奔小康。可是,眼前這個送上門的男人想要干嘛!蘇心妍步步后退,被逼到了墻角:“別以為我救過你……
177.4萬字8.18 142262 -
完結1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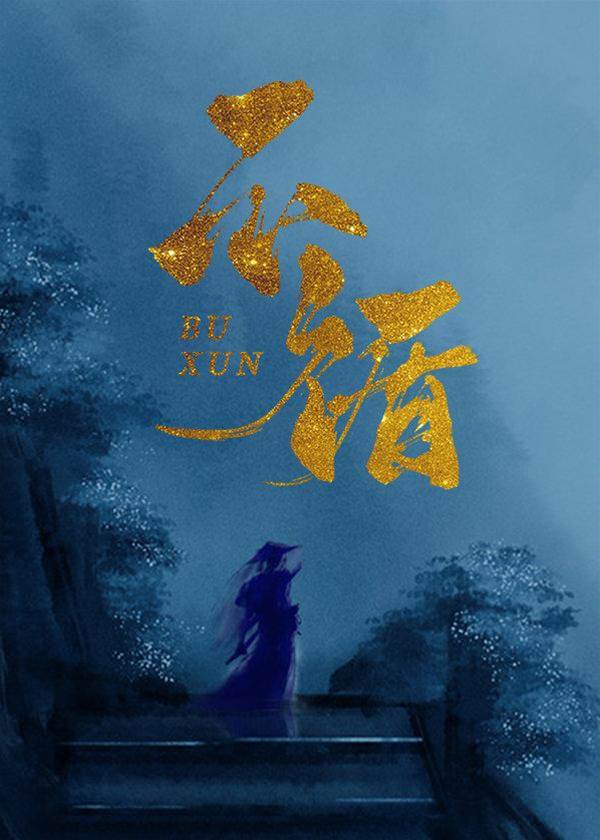
不循(重生)
邵循是英國公府的嫡長女。 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裡的淑妃娘娘是她姑姑,太子之位的有力競爭者三皇子是她表哥。 人生中唯一的不足就是生母早逝,繼母不親,原本應該榮華富貴不缺,波瀾壯闊沒有的過完一輩子,誰知一場夢境打破了一切—— 邵循夢見自己的堂姑為了給兒子剷除對手,犧牲侄女的名節用以陷害風流成性的大皇子,害得自己清白盡毀,只能在鄙夷中被大皇子納為側妃。 大皇子風流成性,大皇子妃善妒惡毒,邵循醒來後生生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誰知這夢做的太晚,該中的招已經中了,無奈之下決定拼死也不能讓噩夢成真,為了躲開大皇子,慌不擇路的她卻陰差陽錯的撞進了另一個人懷裡…… * 邵循清醒過來之後跪在地上,看著眼前繡五爪金龍的明黃色衣角,真的是欲哭無淚—— 這、這還不如大皇子呢! * 1雷點都在文案裡 2年齡差大 3請原諒男主非c,但之後保證1v1
49.3萬字8.33 48807 -
完結187 章

明月映芙蕖
婉婉是盛京第一美人,生就一副嬌若芙蕖、冰肌玉骨的好樣貌 只可惜出身太過低微,十一歲寄居靖安侯府,城中不知多少權貴公子哥兒做夢都想討了她回府——做妾 而靖安侯世子陸珏,玉質表裏、恍若謫仙,更有個皇后姑姑、太子表兄,耀眼奪目放眼整個盛京也無人能及,所以哪怕他一向不近女色,卻依然是城中衆多貴女的心尖明月 兩個人云泥之別,絕無可能 婉婉一直將心事藏得很好,從不曾宣之於口,也不敢在人前表露半分 直到有一天,祖母突然當衆爲她定下了與陸珏的婚事 消息傳出,城中一片譁然,衆人紛紛忍不住開始挖掘這場婚事背後的隱情 婉婉也去主動尋了陸珏,忐忑問他:“表哥既然不願,我們便一同去與祖母解除這門婚事,行嗎?” 誰知陸珏聽了,卻幾不可察地皺了眉,“你既不是我,又怎知我不願意。” * 婚後一日深夜窗外飄雨 閃電過後,身旁原本沉睡的男人忽然伸手捂在婉婉耳邊 雷聲緊隨而至 寬厚的手掌阻絕了轟隆的聲音,她在睡夢中未曾驚醒,只輕輕嚶嚀一聲,更加往他懷裏鑽,夢中囈語“夫君……” 陸珏垂首吻她額頭,“睡吧,我在。”
29.8萬字8 26427 -
完結192 章

引月入懷
太子嬴風假模假樣替三弟搜救未婚妻顧家嫡女,結果一無所獲。 遂冷冰冰蓋棺定論:顧今月“已死”。 事後,一向冷血恣睢的太子殿下破天荒地寬慰傷心的三弟:“斯人已逝,生者如斯。” * 顧今月重傷後失憶,她的夫君嬴風說會幫她想起一切。 “你從前眼裏只有我一人。” “無論我做什麼,你從不推卻。” “唯我是從。” 她紅着臉結巴道:“真、真的麼?” 嬴風握緊她的手,笑得意味深長。 當晚嬴風坐在顧今月床頭,黑瞳貪婪地描摹着毫無防備的睡顏。 驀地俯身湊到她耳邊低笑道:“假的,我也會變成真的。” 顧今月毫無所覺。 直到某夜她從夢中驚醒,記起一切。 她不是他的妻,而是他三弟曾經的未婚妻。 【小劇場】 顧今月捂住懷胎三月的小腹,一隻腳還沒來得及逃出大門。 身後傳來嬴風漫不經心的笑聲。 “嬌嬌,你方向走反了,我在這兒呢。” 忽然被人攔腰抱起送進裏屋,她聽見了刺耳的落鎖聲。
30.4萬字8.18 687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