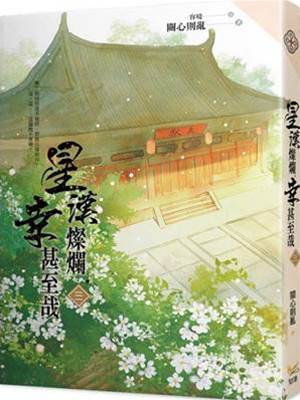《春日暄妍》 ☆45.第45章
第45章
師暄妍的聲音已經細若蚊蚋, 倘若不是寧煙嶼自小耳聰目明能聽八方靜,也未必能聽得見。
那幽微曲折的心思, 讓他一瞬悉。
的點頭,與風月不相關,并不是因為喜歡他才應許,而是因為——負疚,才勉為其難。
寧煙嶼不自認為是君子,充其量,在這個小娘子面前,也只不過是個梁上君子罷了, 幹慣了竊玉香的勾當,也就不覺得自己趁人之危了。
“好啊。”
他輕松寫意的一句“好啊”,卻讓師暄妍心神繃。
擡眸一瞬,瞥見靜謐春山之中, 月華如銀,四下裏春叢隨風擺著纖長的葉稍,年男子眉眼清雋, 墨的發垂落了一綹, 在鬢角邊上, 猶如海藻般微微浮漾。
星眸俊目, 似笑非笑地,看著。
師暄妍簡直手腳都不知道該如何擺放了,只好把發熱的臉頰又垂下去, 本不敢看他。
寧煙嶼握住的玉白蔥, 帶到山腳下, 放鷹臺後不遠的行軍帳。
一座如小丘般膨隆聳立的行軍帳近在咫尺,溪水映著月, 潺潺地繚繞在它的側,軍帳中點燃了燈籠,出明燦的。
師暄妍任由他拉著手,來到這一片軍帳前,低聲問道:“你一早就準備好了嗎?”
寧煙嶼低頭彎下腰,撥開帳簾,帶,邊走邊道:“是讓人在這裏一早準備了些東西,師般般,過來喝藥。”
看起來,太子殿下真是未雨綢繆。
早在打定主意帶出來騎馬時,便把今日要喝的藥已經煨在火爐上了。
被寧煙嶼安置在行軍床上,一不地坐著,因為忐忑,兩只懸在半空的雪足一直不停撞著。
寧煙嶼用幹燥的巾裹著手,從紅泥爐子上把長柄藥罐取下來,倒了一些在碗中,藥湯呈黑褐,飄散著一陣陣的苦味道。
Advertisement
師暄妍嫌棄苦,直皺眉頭,可為了治病,仍是小心謹慎地把那碗藥湯端過來,垂眉低首,小口小口地吃起來。
只是,也太苦了一些。
直喝得皺眉頭。
等乖乖把藥喝完,寧煙嶼低頭,握住的玉指,自的手指間,塞進了一顆包裹著糖紙的飴糖。
師暄妍放下藥碗,攤開掌心,看到這枚晶瑩剔的糖,愣了愣神,眉梢稍凝,又擡眸,看向燈火葳蕤,姿容若雪的男子。
“吃了,能些意。”
師暄妍聽話地點頭,撕開糖紙,把那顆糖含進裏。
飴糖口即化,在舌尖上卷起縷縷的甜意。
停在上方的目,依舊落在自己的上,師暄妍簡直無安。
“出去走走?”
帳中委實太過……悶熱了些,師暄妍的都快要不過氣來了,與其在這裏繼續尷尬地四目相對,倒不如出去走走,師暄妍便委婉提議。
這個建議得到了太子殿下的支持,于是二人便步出行軍帳,走向無邊月下寬闊恢弘的放鷹臺。
男人一路始終無話,師暄妍尷尬窘迫,無意識地談起了放鷹臺的傳說:“傳聞佛陀降生于此,自被風吹雨淋,由狼帶大。也不知道,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有多艱難。佛陀泰然之,對世間一切仍抱有慈悲之心,割喂鷹,終大道。有時候想著前人苦其心志砥礪修行,便覺得自己確實資歷太淺薄了一點,好像浮雲遮眼,為些世俗名利縛,只看得見腳下的路,卻看不見前方。”
寧煙嶼自袖下,握住不安攪的玉指。
側去之時,年男子桀驁清冷的側影,半邊藏匿在夜之中,看得不甚分明,只能約約地察覺到,那只握住自己的手掌,了一些。
Advertisement
師暄妍等著他開口,但寧煙嶼卻什麽也沒說。
他知曉心裏的創痛,恨著那些薄待、甚至苛待的人,也恨著,造十七年來流亡生涯的自己。
他不問,不過是恐懼。
怕又再說起:“寧恪。我討厭你。”
這種懲罰對寧煙嶼而言,太過殘忍了。
所以聰明地,他選擇面對這個話題閉口不談。
終于來到放鷹臺上,綠草芊芊,已經足可以沒過踝骨,尋了一塊幹淨的鋪就石磚的空地坐下,把寧煙嶼的手也攥著,往下扯,他挨著,一同坐在星空底下,這片寂靜得只剩下春風起舞的空地間。
長草拂過腳踝,一寸寸蜿蜒,刮著年男起伏不定的心事。
寧煙嶼看了一眼旁鼻頭有些泛紅的師暄妍,將自己外邊的錦裘解下,為搭在單薄的肩頭。
錦裘間有他上蘭草的芳息,也有他上滯留的溫,便似蠶繭的,朝著的心頭纏上來,撥著那顆不安的心。
漫天星子,徜徉在深邃銀河,也徜徉在他眼中。
“師般般,”他忽而轉眸看向,在這微風清涼的夜晚,眼眸閃著炙熱的,“你曾經說,從來沒想過好活,那現在,你依然堅定于此嗎?”
師暄妍一愣。卻是沒想到,當時說的一句話,寧恪到現在還記得。
這世上,竟然會有人記得說過的話。
屬實令有幾分驚異。
不過,還是坦然地搖搖頭:“不堅定了。早在上你賊船的那天開始,我就不那麽想了。”
寧煙嶼眉眼有些許松。
抱住雙膝,聲音輕輕地道:“現在看來,似乎也不壞。寧恪,謝謝你,沒有讓我後悔。”
年的呼吸也一瞬變得灼熱,眸中亦有些許:“那你過來。”
師暄妍不解:“我不是已經坐在你邊了嗎?”
Advertisement
他要過去,還能過到哪裏去,如何過去?
不待問,寧煙嶼環住了腰,在師暄妍一麻之際,還未曾想到要拒絕,他帶著清幽的蘭草氣息的薄,便吻住了的瓣。
不止是他的,他的手掌,他的氣息,一切一切,都猶如千百萬只螞蟻般,一點點蠶食著搖搖墜的心。
明亮的月下,一柄長桿宮燈歇在兩人的腳邊,照亮著放鷹臺一隅。
春草搖曳的窸窸窣窣的聲,像極了此刻兩人的心跳。
月照著雪白的玉頰,也照著延頸秀項下,逐漸沒蘭苕繡清水芙蓉的小裏,曼妙玲瓏的曲徑,若若現,細看來,那是被兩簇春山撐開的一線深淵。
漸漸地,這吻變了味道。
躺在了放鷹臺上,十指被他強迫著扣。
一只手高高地舉過了頭頂。
長草在春風的慫恿下,一次次地逗弄著的頰、發,和後的,卷起的意。
師暄妍的舌微微發燙。
發現如此這般,好像也……并不討厭。
輕細的貓兒似的嗚咽過後,的眼窩重新如清池般,蓄滿了淚水。
寧煙嶼親了親的臉頰,居高臨下地看,輕聲笑:“師般般,這樣才坐在我邊。”
師暄妍口幹舌燥,早已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來,若是能說話,也必然是罵他的話。
小娘子聲線,他未曾告訴,罵他時,也很聽,很人。
如瀑的青,搭在旁青草上,被月覆上一層和的銀。
風一陣凄,卷得長草急促地搖晃起來。
和的嘆息響在草葉深,猶如弱小的蟲豸蟄伏其中跣足而歌。
那歌聲很遙遠,唱的不知是什麽曲,像是琴曲,又像是舞曲,單調,但并不刺耳,反而十分,細聽來,還有些許的啞。
掃著琴弦的那只手,作漸漸多了幾分急躁。
九天之上皎白幽邃的月,猶如佛陀慈悲的凝視衆生的眼目。
春風狠烈地撕扯著這片寥廓曠原,放鷹臺下,溪水閃著粼粼的月,涓涓地繚繞過長臺,湧向夜中水天相的深。
宮燈被大掌不留神間掃落了,不知落在那裏,風吹過,燈火滅了。
周遭是黑黢黢的,很安靜,闃無一人,唯獨彼此換的呼吸,仍清晰無比。
春叢之中,棲著一雙蝶,振著翅膀,彼此用纖細且長的角一次次試探相。
鴛鴦藤爬滿了木架,那架子很高,搖搖晃晃、忐忐忑忑地立在風裏,也逐漸有了傾塌的趨勢。
終于,月亮藏進了雲端,草葉間轟隆一聲,架子倒塌了,發出了一聲哀鳴。
“師般般。”
耳中落男人低沉沙啞的嗓音。
心弦斷了。
艱難地要爬起來,卻再也爬不起來,齒尖扣著朱,看著他時,目之中有些許埋怨。
寧煙嶼輕聲一笑,雙臂往後,撐起放鷹臺上的青磚,將上撐起來,看著上方的小娘子,角微彎出一點弧痕:“第三十九。”
師暄妍愣了一瞬,才反應過來什麽“第三十九”,暗暗罵他無恥,這些招數縱然不帶書也記得清清楚楚,那不是平日裏沒看麽!
寧煙嶼替將落的錦裘重新搭在肩上,為系好,薄微,在冰冷兇惡的眼神注視之中,道:“夜涼,般般。”
太子殿下道貌岸然,既知夜涼,還非要出來。
師暄妍氣他輕浮孟浪,可想想自己,似乎也并沒好多,便是罵他,也沒底氣,靜靜地看了他半晌,自己將衫收拾妥帖,道:“我要回去。”
寧煙嶼後背也出了一層汗,涼風吹過,也正覺得有些涼,應許了,誰知才扶著起,這黑夜之中,竟閃過一雙幽幽的黑瞳。
寧煙嶼心神一凜。
只見一頭龐然大,正悄然朝這裏靠近。
師暄妍也看到了,幾乎是在看見的一瞬間,朱哆嗦著口而出:“不好。是熊羆。”
那麽大一頭熊在靠近,而方才,兩個人是全然忘我了,竟毫沒有察覺。
寧煙嶼將護在後,警惕面前黑熊的一步步靠近。
龐大的軀在春風的草葉間,帶著危險的氣息,逐漸走近。
寧煙嶼彎腰拾起地面上的長柄宮燈,覺到,著自己後背的那顆心,幾乎快要蹦出嚨眼了。
在野外遇到野雖然不多,但若不幸真的遇到一兩只,也不算什麽稀罕之事。
寧煙嶼并不是毫無準備,行軍帳駐紮之,有暗衛在守候。
唯獨只有師暄妍。
他警惕著黑熊的靠近,對師暄妍沉著冷靜地命令:“你在我後,往後退,等那頭熊撲向我之後,即刻便跑。”
說完,又怕張,語調和緩些:“注意腳下,莫要摔倒。”
師暄妍一不敢,聽他這麽說,更是不口而出:“那你呢?”
寧煙嶼失笑:“師般般,你放心,你不會做小寡婦的。”
想,這撐死不過是個門寡。
他們都還沒婚。
那他,他不會有憾嗎?
“後退。”
寧煙嶼已經收斂了玩笑,沉聲命令。
師暄妍的心嚇得發抖,本來就肚打,更加是離開得踉踉蹌蹌。
不敢與那頭熊瞎子對視,只一步一步,忐忑而謹慎地往後退。
說時遲,那時快,那頭黑熊突然盯住了它的獵,朝著寧煙嶼加快了腳步,撲了上去。
師暄妍幾乎不敢看,一眨眼之間,聽到寧煙嶼吼:“跑!”
師暄妍掉頭就跑,沒有任何猶豫,迎著風,跑向山腳下那亮著燈的行軍帳,一邊跑,一邊喊人。
單人,甚至連匹馬都沒有,寧恪縱然再懷武藝,如何能鬥得過一頭年黑熊?
師暄妍的心不知為何堵得厲害,也許,也許寧恪就是這世上唯一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真心對的人了,如果他真的有不測的話……
發誓,這輩子再也不會嫁人了,再也不會。
可是,師暄妍合該就是這樣的命嗎?
以為,和寧恪是一場孽緣。
寧恪對不起,害本該平順普通的一生,變得步步險象環生,好不容易,從泥沼裏掙紮出來,被迫和他捆在了一,這麽快,就連他也要失去了嗎?
那這一生,便真是個天大的笑話。
不知何時起,已跑得面目模糊,臉頰上全是淚水,一口氣,終于奔到了行軍帳下,氣沒過來,便對著暗衛擺手:“殿下……遇熊……救他……”
猜你喜歡
-
連載337 章

獵戶農妻寵上癮
一覺醒來,竟成了古代某山村的惡臭毒婦,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就算了,還被扣上了勾搭野漢子的帽子,這如何能忍? 好在有醫術傍身,於是,穿越而來的她扮豬吃虎,走上了惡鬥極品,開鋪種田帶領全家脫貧致富的道路。當然更少不了美容塑身,抱得良人歸。 隻是某一天,忽然得知,整日跟在身後的丈夫,竟是朝廷當紅的大將軍……
58.4萬字8 5668 -
完結17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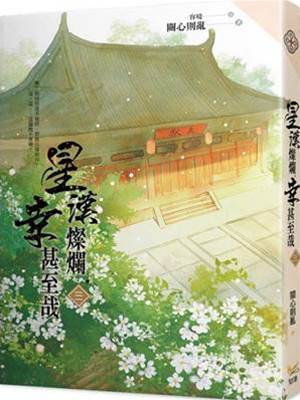
星漢燦爛,幸甚至哉
許多年后,她回望人生,覺得這輩子她投的胎實在比上輩子強多了,那究竟是什麼緣故讓她這樣一個認真生活態度勤懇的人走上如此一條逗逼之路呢? 雖然認真但依舊無能版的文案:依舊是一個小女子的八卦人生,家長里短,細水流長,慢熱。 天雷,狗血,瑪麗蘇,包括男女主在內的大多數角色的人設都不完美,不喜勿入,切記,切記。
90.7萬字8 5631 -
完結80 章

再嫁
破鏡可以重圓?她不愿意!世人皆說,寧國候世子魏云臺光風霽月,朗朗君子,明華聽了,總是想笑,他們怕是不知,這位君子,把他所有的刻薄,都給了她這個原配結縭的發妻。而她唯一的錯,就是當初定下婚事時未曾多問一句罷了。誰能想到,讓魏云臺愛慕至極,親自…
31.3萬字8.17 48598 -
完結331 章

寸寸歡喜引相思
她本是西楚國侯爺之女,因一碟芝麻糕與東陽國三皇子結下不解之緣。卻因一場府中浩劫,她逃生落水,幸被東陽國內監所救,成了可憐又犯傻氣的宮女。一路前行,既有三皇子與內監義父的護佑,又有重重刀山火海的考驗。她無所畏懼,憑著傻氣與智慧,勇闖後宮。什麼太子妃、什麼殿下,統統不在話下!且看盛世傻妃如何玩轉宮廷、傲視天下!
82.6萬字8 855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