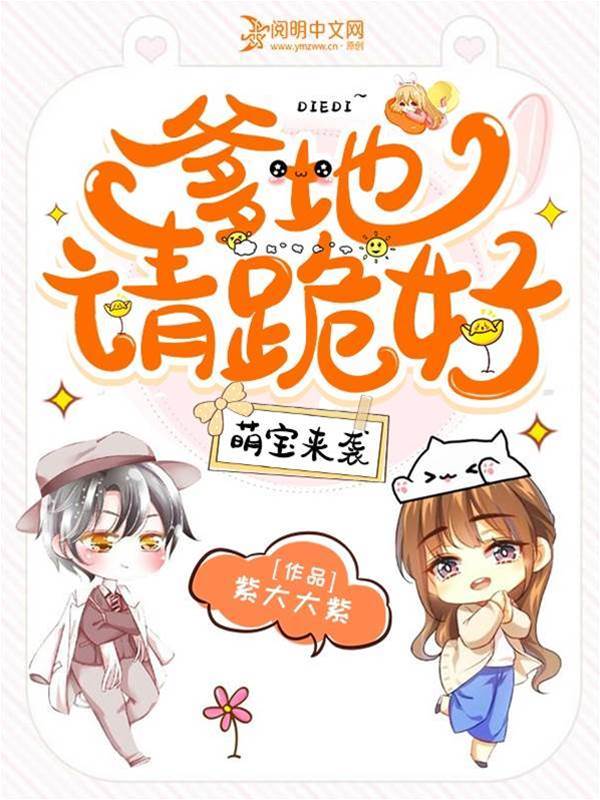《第12次擁抱看不見的你》 026章 散落的筆記本
一頂帽子沒找著?
“哥。”瞪大雙眼的薛栩栩一把拽住薛江山的袖口,“哥,你剛才說什麼?什麼做有頂帽子沒找著?”
薛江山對薛栩栩過激的反應不甚明白,他低頭看了眼那雙頗為張抖的手,手腕一轉便反握在了手心。
他笑了笑,試圖安自己妹妹的緒,“嗯,媽的那頂帽子沒找著,可能是被我當時順手丟進其他東西里面,一起給燒了。”可能是自責自己的失誤,薛江山又補充了句,“栩栩,對不起是大哥大意了。”
可是,薛栩栩卻木訥地搖了搖頭,“不是的、不是這樣的……”
“栩栩,你是哪兒不舒服嗎。”
面對薛江山的關切,薛栩栩陷了恐慌之中,因為分明記得打開箱子的時候,里面放著的是兩套服兩頂帽子和一張相片。因為匆忙所以帶走了一頂帽子,因為偶然又將那頂帽子留在了冰棺里……現在回來了,不僅帽子不見了薛江山的記憶也發生了改變。
也就是說,不僅能回到過去,還能改變現在?
“栩栩。”老半天得不到回應的薛江山終于忍不住輕輕地推了推薛栩栩。
而回過神來的薛栩栩似乎也想要告訴薛江山這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
但,話到了邊又給咽了回去。
調轉視線看向別,又撐著薛江山的手站了起來,“哥,我沒事兒,可能就是太困了。我想下去休息一下就好了,晚上吃飯就不用我了。”
說完,薛栩栩又看了一眼那個被打開的箱子,不住彎下腰去翻找了一遍確信真的就只有一頂帽子而已。
站在柜前的薛江山蹙著眉頭很是不解地看著薛栩栩讓人起疑的舉,沉了一會兒挽上手臂抱在前不確定地問道,“栩栩,你是不是想起什麼了?”
Advertisement
“想起什麼?”薛栩栩也不明所以地反問。
但薛江山的目里又太多的探究與打量,使原本心里有鬼的薛栩栩不堪重的逃避對視,閃躲目,叉腰撓頭做著一些多余而不安地肢作。
“算了。”薛江山抬手拍了拍薛栩栩的肩頭,勾一笑倦意濃烈。
他彎腰把被薛栩栩翻出來的收納箱按原樣都放了回去,沉重的木箱子也依舊在最下面。弄好后,拍了拍手就徑自出了門,整個過程沒有同薛栩栩流,哪怕是一個眼神。
這讓薛栩栩覺得慌,加之剛剛發生的一切,都讓覺得不安極了。
回到臥室后的沒辦法讓自己冷靜下來,第一時間就給王昊去了個電話,張口就問,“你認識沈勵揚嗎?”
那邊愣了許久,久到薛栩栩開始懷疑或者現在的所有都已經出現了變。
可是。
電話里面的人咳了咳,“栩、栩栩,你怎麼了?”
仍是王昊的聲音,薛栩栩的心便沉了一分。
似不依不饒地繼續問道,“你認識沈勵揚嗎?”
“……”王昊,“認、認識啊。”
“他還是警察?”
王昊愕然,“當然。”
薛栩栩,“……”
“栩栩,你到底怎麼了?”太莫名其妙了,王昊忍不住疑。
薛栩栩頓了頓,到底只是回了句,“這件事見面再說。”
見面的時間約在了三天后,并非薛栩栩不急迫,而是下意識的。
見到王昊的時候,薛栩栩終于把回到江城以來發生的事都給他說了一遍,更著重說明第二次被吃掉的餃子以及被自己放進冰棺里的帽子。
事實難以相信。
聽完之后的王昊張著瞪著兩只圓溜溜的眼睛,好像很震驚但模樣卻稽可笑。
薛栩栩看了他一眼,從包里把那塊時針表放到桌上,“你說過,這塊時針表是我送給沈勵揚的,但是在我的記憶里本就沒有這塊表的存在。”
Advertisement
王昊將那塊表拿在手上一瞧,時針指在八點的位置上,跟薛栩栩說的很是相符;他手試著調了調指針。
真的,怎麼都不了。
他將表輕輕地放回桌上,收回手夾在兩膝蓋中箭,一雙眼珠得轉悠了半天,再看向薛栩栩時,才有些哆嗦地回道,“我是相信科學主義的。”
聞言,薛栩栩竟是噗哧一笑,也回答道,“我也相信。”
只是三番五次發生的事顯然已經超出了所謂科學的范疇。薛栩栩沒說話,也沒將時針表收回去,依舊等待著王昊全盤接后的回答。
王昊見薛栩栩不言,自己也繼續看向表,“表的事兒,好像還是你們倆沒鬧分手之前聽勵揚說的。那晚我跟他在宿舍里喝酒,我無意之間看到了這塊表,很特別就多問了一句,他就說是你給的,后來過了沒多久你們就分了。”
說完,他將桌上的表推了推,“栩栩,雖然你說的事不可思議,但是我想你不會拿勵揚的事兒來開玩笑。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什麼嗎?”
原諒為刑警的王昊此時此刻還得讓薛栩栩拿主意,畢竟匪夷所思的關鍵人是。
薛栩栩,“……”
叮鈴一聲,快餐店的門被拉開。
王昊警覺地往門口看了一眼。
一看,臉上神陡然一變,“栩栩。”
薛栩栩見狀轉過頭去,便看到姜好冷著一張臉快步朝他們這個方向走來。
走近,看清王昊的長相時臉上的表更是不善,以致于原本站起來手問好的王昊也尷尬地愣在了當場。
“去你媽的!”隨著姜好一聲暴喝,平日里溫文爾雅的他直接朝王昊臉上送上了拳頭。
一時不察,王昊結結實實地挨了一拳跌靠在了墻上;姜好又沖了過去,薛栩栩攔著可奈何本拽不住發狂的姜好。
Advertisement
但王昊到底有手,怎麼可能白白挨第二下,基于上還穿著警服呢,他迎上前來迅速用上擒拿手,一招就將姜好反扣在了桌子上。
“老實點!”王昊用舌頭頂了頂角,無奈地看向薛栩栩。
在超市時,王昊是見過姜好的,也知道薛栩栩要結婚的事,自然也猜到兩人的關系;至于姜好為什麼會打自己,反正也都是八九不離十。
雖說行得正做得直,但王昊也明白因為自己多事把沈勵揚的日記跟時針表寄給了薛栩栩,才有了這一切的開頭,才讓已經準備結婚的薛栩栩被徹底卷了進來。
有些對不住,但也不會道歉,是以王昊讓薛栩栩做決定。
薛栩栩回看了他一眼,“麻煩你了,你先回去吧。”
王昊點點頭,又看了眼還在抵死掙扎的姜好,擔憂道,“你小心點,有什麼事隨時電話聯系。”
“好。”
王昊小心松開姜好的手,走時還頗為凌厲地瞪了他一眼以示警告。
看著大步離去的王昊,又瞧了瞧店里議論紛紛的店員和不多的食客,薛栩栩撿起剛才被掃到地上的時針表,小心看了眼后就放進了包里,然后頭也不回地往外走了。
姜好轉了轉吃疼的手腕,埋下頭迅速地跟了出去。
薛栩栩走出快餐店,快速地在周圍掃了一遍,果然看到了街角那輛眼的A6,朝街角走去,可僅僅踏了兩步就被人拉拽著手肘往后拖。
“你放開我!”薛栩栩提著高跟鞋就準備往姜好的鞋子上踩。
但那人似乎本不在乎薛栩栩的憤怒,全然跟平時是兩個模樣。他不管不顧地拽著薛栩栩上了車,強行關在了副駕駛,自己也坐上主駕啟飛奔著開了出去。
進到車里,薛栩栩也沒鬧,鼓著一張小臉冷冷地盯著前面不斷被他們超過的車輛。那速度,竟然一點都不覺得害怕,甚至期待著出一場什麼事故。
可能是瘋了吧,居然生出了這樣的想法。
自嘲似的勾著角笑了,邊上的姜好瞟眼看來,心底的怒氣持續上漲。
一路疾馳,姜好的駕照估計得回收了,不過已經對他來說好像已經不再重要了。
他將車急剎在了江邊上,下了車嘭的一聲甩了車門。
差點撞上擋風玻璃的薛栩栩了額前的發,提起上的包無畏地走了下去。然而,卻并不是為了要跟姜好談心聊天。
叉腰站在江邊上半天沒見靜的姜好,轉頭一看,薛栩栩已經噔噔噔地朝著來時的路走了。
“栩……薛栩栩!”
薛栩栩聞聲站住,轉回頭去好似陌生地盯著他看。
姜好連步趕了過去,雙手舉過頭頂煩躁地在頭發里,“你不解釋嗎,就不需要跟我說點什麼嗎?”
“那你想聽到什麼?”薛栩栩反問,見他不答,一笑,“姜好,我解釋了,我說了你就能收起你的懷疑嗎。”
“可是那個人……”他放下手來,目頓時暗了下去,“你還是想著他對不對?”
這一問,薛栩栩不知該如何作答,實話實說只怕姜好會更惱,但薛栩栩不喜歡說謊。咬咬牙,“姜好,我從來沒有搖過跟你結婚的想法。”
“可你還是著他。”
“我知道自己很任,但是我需要給自己和沈勵揚一個待……”
“待什麼?”姜好暴地打斷的話,“待你有多他,他有多你嗎!待你們而不能相守的痛苦嗎!待我就是個足你們偉大的小三嗎!”
“你能不能好好說話!”
“不能!”姜好吼道,“我人都要跟人跑了,我還能好好的嗎!你知不知道我忍得有多痛苦!薛栩栩,為什麼你就不能把目放到我的上,為什麼就不能可憐可憐我!”
“……”這一點,薛栩栩無法否認,對于姜好自己是太忽視了,可是今天跟蹤無故手打人實在太出乎的意料,片刻間也難以理解。“我又沒干什麼對不起你的事兒!我跟誰跑了?你倒是把話說清楚啊!姜好,你能男人點嗎!”
“我他媽還不男人嗎!”因為憤怒,姜好揮了膀子,雖沒挨上薛栩栩但卻將的手包給掀在了地上,東西撒了一地。
他吼道,“當初是他自個兒放棄跟你出去選擇留在了江城,因為你,我放棄了多名牌大學陪你一起去念了個三流的大學,至今工作升職總比別人矮一截。也就因為沈勵揚一句話,我沒趁人之危本本分分當個朋友替他照顧你,這樣我還他媽不夠男人嗎!”
薛栩栩一怔,竟不想當年還有這樣的。
垂下頭去,看向地上散落的隨用品,下意識地蹲下去撿。
姜好又煩躁地了頭,忽然掃到腳摔得有些遠的一個本子,可能把憋在心里太久的話一口氣吼了出來,人也輕松了,跟著就生出一擔憂來。
他抿著走過去彎腰去幫忙撿本子,第一次沒功兩指剛沾上封面就給了,第二次又嘗試著,卻看清了無意被掀開的第一頁紙,上面寫著:沈勵揚。
猜你喜歡
-
完結71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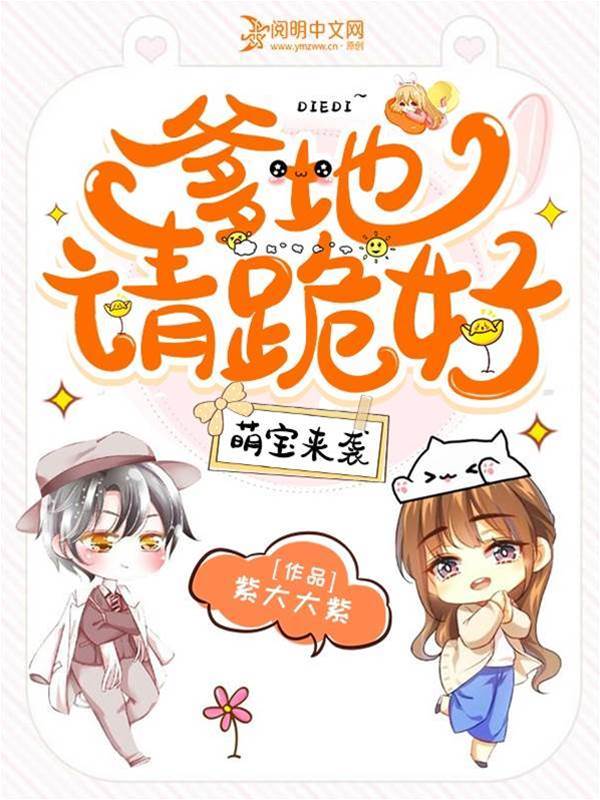
萌寶來襲:爹地請跪好
她在家苦心等待那麼多年,為了他,放棄自己的寶貴年華! 他卻說“你真惡心” 她想要為自己澄清一切,可是他從來不聽勸告,親手將她送去牢房,她苦心在牢房里生下孩子。 幾年后他來搶孩子,當年的事情逐漸拉開序幕。 他哭著說“夫人,我錯了!” 某寶說“爹地跪好。”
129.7萬字8 24178 -
完結76 章

溫柔刀by夢筱二
黎箏二十二歲那年,喜歡上傅成凜,他是她小叔朋友。 生日當天,小叔送給她一家公司的股份當禮物,公司老板恰好是傅成凜。 她開始打小算盤,想以股東身份“潛規則”傅成凜。 傅成凜提醒她一個殘酷的事實“你只持有0.1%的股份,這點股份可以忽略不計。” 黎箏“......” 之后發生了什麼,只有助理知情。 那天黎箏來找傅成凜,離開后,傅成凜讓助理買口罩。助理發現老板的嘴唇被咬破,腫了。老...
28.9萬字8 15475 -
連載168 章

夫人提離婚後,商總戀愛腦覺醒
【虐戀 暗寵 雙潔 先婚後愛】夏恩淺的白月光是商頌,十年暗戀,卻從未有過交集。知道他高不可攀,知道他寡涼薄情,也知道他有未婚妻。一朝意外,她成了他的新娘。她從沒奢望,卻又想賭一把,最終,還是高估了自己。她流產,他在陪別人。她最愛的親人去世,他在陪別人。她被當眾欺辱人人嘲笑,他身邊護的還是別人。……當所有人都說她配不上他。深夜,夏恩淺丟下一紙協議,心如死灰,“商頌,你根本就沒有心。”男人死死攥著她要離開的手,眼裏翻滾著灼熱和偏執,嗓音嘶啞,“夏恩淺,沒有心的一直都是你……”
31.3萬字8.18 16026 -
連載483 章

前夫,認輸吧!我身價千億你高攀不起
陸知薇和沈矜墨做了三年契合無比的夫妻,白月光的出現將婚姻的平靜徹底打破。陸知薇不哭不鬧,丟下一紙婚約,回歸豪門繼承億萬資產去了。男人哪有搞事業香。賽車場,她是最
89.2萬字8.18 10979 -
完結310 章

紅玫瑰的小王子[嬌夫]
文案:★正文已完結,番外不定時掉落中~(^ω^)★★斯文敗類女菩薩x清純釣系白蓮花★【全校炸裂版文案】全校都知道,大一新生李衍,寡言少語,清清冷冷,窮得叮當響,天天去打工,是個除了美貌一無所有的藝術系冰塊。全校都知道,大四學姐程之遙,穩重自持,平易近人,如春日豔陽般溫暖,也如高山雪蓮般遙遠,是個德才兼備全面發展的理工科天才。全校都無法將這兩個完全不相同的人聯系在一起。直到有一天,有人看見穩重自持的學姐將清冷木訥的學弟逼到牆角,摁在牆上,眼尾發紅,聲音低啞,對著臉紅得像開出一朵花的學弟說:讓我親一下,命都給你。全!校!都!炸!了!【知情人士透露版文案】01李衍第一次見學姐,學姐救了跌倒的他;李衍第二次見學姐,學姐救了迷路的他;李衍第三次見學姐,學姐救了被奸商師兄坑蒙拐騙的他……李衍:事不過三,學姐救我數次,我該怎麽回報呢?學姐:舉手之勞,無須回報。李衍:不圖回報,那學姐為什麽屢次三番救我于水火呢?學姐禮貌微笑:大概是因為你臉白,長得好看吧。………………李衍深夜攬鏡自照,思忖:難道,是要我以身相許?他糾結了。一個清純男大學生,還沒有做好戀愛的準備。※※※※※※※※糾結數日後,李衍終于下定決心獻上自己。他羞答答地向學姐送上一支愛的玫瑰:學姐,能請你吃晚飯嗎?學姐看看眼前的玫瑰,又看看他,笑容比三月的春風還溫暖。她說:抱歉啊,晚上要跟男朋友吃飯呢。02順手幫了個小學弟,對方就開始對她暗送秋波。程之遙扶額。魅力太大,不是她的錯。面對又高又瘦又白又清純的學弟的一次又一次勾引,她不為所動。只因她是一個富有責任心的好學姐,不能讓學弟陷入愛情,耽誤了學業。——絕對不是因為學弟身材像個未成年白斬雞。快刀斬亂麻打退了學弟懵懂的試探,程之遙為自己的高尚而感動落淚。——直到一個寒假過去……白斬雞學弟健身歸來,變身陽光美少年!正是她愛的那一款!程之遙:……程之遙:好久不見。別秀了,看到你腹肌了。程之遙:今晚要一起吃晚飯嗎?程之遙:男朋友?什麽男朋友?不好意思我單身。程之遙解釋,自己并非見色起意。只是想在畢業前,創造一些關于校園的浪漫回憶。什麽?你問畢了業怎麽辦?傻瓜。她笑。畢業分手很正常啊。※※※※※※※※浪漫數月後,程之遙覺得是時候了。——是時候跟這個膚白貌美、器大活好、身嬌體軟、八塊腹肌、溫柔體貼、善解人意、百依百順、容易推倒、上得廳堂、下得廚房、勤儉持家、吃苦耐勞、還全心全意支持她創業的尤物說分手了!畢竟男人只會讓她沉迷溫柔鄉,擋住她逆襲的路。但是這個可怕的男人,竟然挑不出缺點,找不出理由說出分手二字!簡直恐怖如斯!沒辦法,只能……程之遙把學弟的兜掏空,又把自己的兜掏空,把所有錢堆在一起,還不足一百塊。望著眼前一堆鋼镚,程之遙沉痛道:創業有風險,投資需謹慎。學姐我創業失敗,沒錢還債。你窮我也窮,兩人難湊一百塊,不能這麽苦哈哈地談戀愛。咱們從此各奔天涯,好聚好散,相忘于江湖,永不再見!——————多年後,程總坐在她五千平大別野的豪華露臺上,眺望著蒼茫夜色下她龐大的商業帝國的時候,準能想起她跟學弟提分手的那個遙遠的下午。在蜜一般的夕陽下,少年清澈的眼裏寫滿了擔憂。只見他低下頭,從破到掉渣的舊錢包裏,掏出一張銀行卡,塞到她手中,說出了那句讓她震撼終生的話——“一個億夠不夠,不夠我再去籌。”#旺妻命##她好我也好##努力男孩最幸運#【強行文藝版文案】“花兒張起她的四根刺說:老虎,讓它張著爪子來吧!所有人都笑了起來,就連小王子也不相信。因為她只是嬌弱的玫瑰而已,卻吹噓能與老虎對抗。多麽虛榮,多麽自不量力……”[注1]“可是,她說的是真的啊。”懷中人疑惑擡頭,“玫瑰花盛開的地方,到處都是尖刺。這就是老虎不敢涉足玫瑰園的原因。”講故事的聲音頓住。陽光明媚,一切陰霾皆已驅散。她合上書,執起他的手,低頭深深望進他的眼裏:“而這,就是我愛你的原因。”[注1]該故事來源于聖埃克蘇佩裏《小王子》。部分文字有改動。內容標簽:情有獨鐘天之驕子業界精英商戰逆襲姐弟戀程之遙李衍其它:嬌夫,姐弟戀,天作之合,女強一句話簡介:清純學弟一見學姐誤終身立意:吾心安處是吾鄉
85.9萬字8 18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