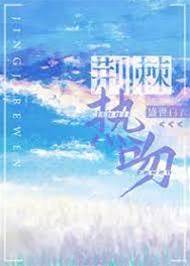《深淺》 第13章 不生氣了好嗎
付霽深的車停地比較遠,在一個路燈下面。
夏日的蚊蟲繞著燈在飛,晚風里燥熱尚未完全褪去。
黎淺走過來廢了一番功夫,后背的服有些,黏在上很不舒服,但是看到付霽深時,還是扯了一記明艷的笑:“付總又見面啦!”
有點微,紅特意重新描繪過,烈焰、張揚。
他的一側臉浸在黑暗里,骨相實在優越,有棱有角,立鋒利。黎淺很迷他運時熱汗順著下頜骨的線條順延至脖頸甚至再往下的覺!
很帶勁!
“和他做過?”
“嗯?”黎淺眨了眨眼,似乎不太明白他的意思。
付霽深笑了下,很晦,一側的弧度全在黑暗里,黎淺卻從那漫不經心的笑意里,讀懂了一不善。
“誰更棒?”
他手臂抬起,肆意冷懶地往車頂一擱。
黎淺才看到他指間夾了煙,沒怎麼,或許是剛點燃,猩紅的煙頭忽明忽暗。
Advertisement
再裝傻就沒必要了,黎淺斂了笑意,先做了個深呼吸平復了緒,然后才回他:“付總想聽什麼答案?”
付霽深覷一眼:“憑你自己的覺說說。”
似乎有勁在暗拉扯著,緒翻涌。
黎淺覺得自己很奇怪,奇怪明明知道付霽深是個什麼樣的人,卻不知從幾時開始,會被他一兩句話刺到。
夜風裹著的熱意,讓人繃到極致的緒徹底崩裂,黎淺勾了勾,往前走了一步:“那,應該是劭。。。”
“呃!”
黎淺本沒機會把話說完,下一秒就被人住脖子抵在了車上!
“付總很在意這個?那我換個回答。”像個妖,會勾人會挑撥的妖,故意刺激他:“邵醫生更棒!”
付霽深是真被給惹到了,下手就完全沒顧上的。
黎淺痛的整個人都起來,“付霽深你他媽是不是畜生?!”
Advertisement
這是第一次罵他。
罵出口的時候,痛地還沒緩過神來!
越罵越掙扎,付霽深就越是下狠手,他就想痛死!
黎淺指甲都抓壞了,指里是抓破了他背脊浸進去的,后來他松開,黎淺也不掙扎了,聽到他涼薄的著冷意的聲音:“他知道你這破鞋樣兒嗎?”
黎淺不搭理,閉著眼,眼角有淚痕。
的不反抗不回應反而激怒了他,付霽深一把抵住下頜,用碎那樣的力道:“黎淺,你他媽以為自己是誰?!”
“威脅我?玩我?你也不看看你自己配不配!!”
。。。
車的氣氛沉悶,像頂的烏云。
“對不起。”
好久。
黎淺聽到自己的聲音。
破碎、沙啞。
錯了。
費了那麼多心思,好不容易走到這一步,不該沖的,不該為了報復他的毒舌說那些話。
“我跟邵醫生什麼關系都沒有。”車沒開燈,外面的路燈進來一點昏暗的線,落在掌大的臉上,特別蒼白。
Advertisement
黎淺努力爬坐起來,攏了攏長發,出一張干凈的臉,甚至努力微笑:“我其實剛才就是有點生氣,生氣你會說那種話。”
“下次不會了。”深呼吸,看他被抓破的傷口:“疼嗎?我去買點藥。”
自始至終就是在說,付霽深完全沒有搭理。
此刻的黎淺,乖順地像一只貓,貓兒抬起的下枕在他的肩膀,手指在他口畫圈:“不生氣了,好嗎?”
猜你喜歡
-
完結1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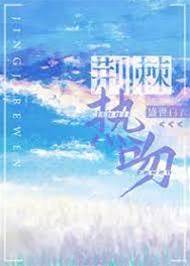
荊棘熱吻
季弦星有個秘密,她在十六歲的時候喜歡上了一個人——她小舅的朋友,一個大她八歲的男人,后來,無論她怎麼明示暗示,鐘熠只當她是小孩。她安靜的努力,等自己長大變成熟二十歲生日那天,她終于得償所愿,卻在不久聽到了他要訂婚的消息,至此她一聲不響跑到國外做交換生,從此音訊全無。再見面時,小丫頭長的越發艷麗逼人對著旁邊的男人笑的顧盼生輝。鐘熠走上前,旁若無人的笑道:“阿星,怎麼見到我都不知道叫人了。”季弦星看了他兩秒后说道,“鐘先生。”鐘熠心口一滯,當他看到旁邊那個眉眼有些熟悉的小孩時,更是不可置信,“誰的?”季弦星眼眨都沒眨,“反正不是你的。”向來沉穩內斂的鐘熠眼圈微紅,聲音啞的不像話,“我家阿星真是越來越會騙人了。” 鐘熠身邊總帶個小女孩,又乖又漂亮,后來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那姑娘離開了,鐘熠面上似乎沒什麼,事業蒸蒸日上,股票市值翻了好幾倍只不過人越發的低沉,害的哥幾個都不敢叫他出來玩,幾年以后,小姑娘又回來了,朋友們竟不約而同的松了口氣,再次見他出來,鐘熠眼底是不易察覺的春風得意,“沒空,要回家哄小孩睡覺。”
51.8萬字8.18 232480 -
完結38 章

脫軌
不接吻、不留宿、不在公開場合調情……這是他和她之間的規矩。不管床上如何,床下都應時刻保持分寸;關于這一點,余歡和高宴一向做得很好。直到余歡所在的律所新來了個實習生,而人那正是高宴的外甥——事情開始脫軌。
6.1萬字8 318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