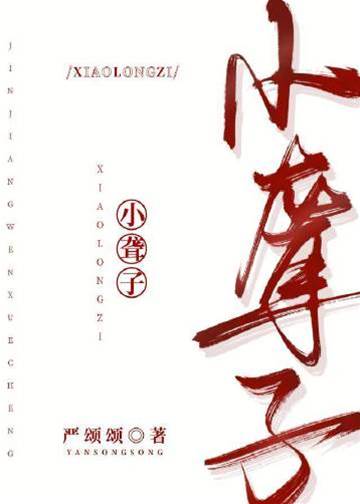《民國小商人》 第164章 滬市探親白九規規矩矩坐在對面,問什……
過年之後, 蜀地謝家連著上了一月有余的報紙。
白、謝兩家的合作開始有了進展,這次不再是外頭穿著的小道消息,而是正兒八經登報聲明。
兩家一起合開了船舶公司,江上新增的十艘江海巨頗為引人注目, 兩家開了新航線, 之前白家在湘江、萬江地拿下的幾碼頭和西川謝家的航線連接起來, 開闢更快捷便利的航線,運送地點更遠, 也更迅速。除了原本的貨生意,還增添了客,用作民生之用, 新船在江面上鳴響汽笛行駛的時候, 還上了報紙,引起了一陣熱議。
白謝二家趁熱打鐵,新開的客運公司賣了好些艙房船票,這些船票分三類,高中低價格的都有, 叟無欺, 服務態度也好, 船上乾淨衛生,座椅艙房收拾得整潔明亮,也是江上第一家包餐食的客,了當時的新風尚, 很多人都慕名去坐一趟船。
大致定下來之後,九爺留了兩個人在這邊理辦廠事宜,自己則帶謝了一趟滬市。
謝頭一運鹽,謝泗泉再不放心也不能阻止, 畢竟這事兒以後早晚也是謝接手,來想去,只能多派了幾個手下心腹跟著,一路幫著鋪平道路,能多照顧一點算一點。
這次在江上行船,以往心又有所不同。
船行程過半,兩岸風景變了許多,山崖漸緩,不再崎嶇。
滬市。
謝去了福泉莊接鹽貨,他是東家,這次謝泗泉放開手讓他去做,也有讓下頭各位大管事多謝接的意思,以後西川生意謝接的還多,總要多磨合一二。
九爺備了厚禮,先一步去見了賀東亭。
Advertisement
賀東亭人清瘦了許多,眼窩有些凹陷下去,邊跟著一位醫生,九爺來的時候他也沒有避諱,客氣地讓他在一旁,打過針之後才請客人座。
賀東亭道︰“有些簡陋,還勿見怪,這幾日不適,一直睡不好,也只有這個房間落地窗大,好一些,能睡個好覺。”
白九問起病癥,賀東亭也隻推說是舊疾復發,並沒多說什麼。
白九道︰“去年在西川擺喜宴,兒還問起您,當時就十分擔心,只是舅舅說不礙事也攔著沒讓來探,若是知道如此,他一定早就過來了。”
賀東亭笑道︰“是我讓謝泗泉別說的,我那會病得有些重,一時也不知道能不能好,所幸熬過冬日,如今有了幾分起『』,還能多陪兒一段時日。”
白九又問︰“這病有多久了?”
賀東亭︰“有一段時間了。”
白九︰“可想過其他辦法?”
賀東亭搖頭,笑道︰“老『』病,治來治去,也不過就是那幾句話,聽得膩味了。”他輕輕嘆了一聲,環視周,視線帶了暖意,“在這個房間,我住得安心些,總能記起以前。”
白九抬頭,看到這房間裡有一些老件,像是府裡主人以前留下的品,一旁帽架上還有一頂絨線帽,若不是款式『』都已泛白發舊,看起來仿佛主人剛去出去喝茶,馬上就要來一般。他略一打量周圍,心下了然,這是以前謝沅留下的東西,或許這個房間,就是賀東亭特意為夫人留下的。
睹思人,聊作藉。
上次白家一行蜀地,賀東亭一路同行跟隨,九爺也曾和他攀談過,雖說不上投緣,也彼此欣賞。只是這次賀老板顯然沒有上次那麼有神,說話的時候有些疲乏,走神幾次。
Advertisement
直到賀東亭聽說謝也來了滬市,這才打起了幾分神,說要著。
白家帶來的那份禮單,賀東亭也只看過一眼,沒什麼反應,惟獨其中一份讓他眼前一亮。那是一盤殘棋,白九來來找賀東亭,邀他對弈。
白九對賀老板心態握地準,隻一句“這是昨夜兒未能破解之局”就讓賀東亭座,心甘願抬手執子。
賀東亭棋藝不錯,下棋時很說話,更多的是在觀察。
觀察對方,也在小心落子。
賀東亭下棋走一步看三步,他落子緩慢但堅定,很快就察覺,若他下得慢了,對面也跟著出棋慢一些,若他下得快,對方也跟著加快速度。他抬頭看了對面坐著的年輕人,問道︰“你已解了這棋局?”
白九淡聲道︰“未曾,只是從昨晚到現在多想了半日,略有所悟。”
這話說得隨意,若放在平時賀東亭不會多在意,現在聽了頗不是滋味。
他之前在西川城想了幾天,怎麼想,都是自己棋差一招,何嘗不是輸在了時間上?他見到謝的時候對方已經長大,陪在邊教導的人也是白九,他早已沒有資格站在旁邊提什麼意見了。
賀東亭嘆了口氣,隨意放下一枚棋子,緩聲道︰“這棋局,我也破不了,兒下了半局,後面也只能順著他的路子往下走。”
下完棋,賀東亭對白九的態度也改變了幾分,招呼人要拿些酒來對飲。
白九攔住道︰“換些茶來吧,兒囑咐過你不好,不讓飲酒。”
賀東亭心裡寬,點頭應了,又問道︰“說起來今日我還未見到兒,他去哪裡了?”
“去了福泉莊,舅舅如今想把家裡的事給兒打理,慢慢讓他接手。”白九代為解釋道。“另外還要陪黃先生跑一趟,上次北平來的那些教授發現了不古籍,黃先生代為寫了注文,其中有一冊為遊記,先生特意繪製了山川河流圖,需要送去整理造冊,想必書局有些忙,要再一會才能過來。”
Advertisement
賀東亭哦了一聲,茶水小點心送上來之後,兩個人臨窗坐著,一邊喝茶一邊聊天。大約是心態發生了微妙的改變,賀老板現在已經徹底放下“管”這一個字,滿心只有順著兒子的念頭,坐在那和白九說話的時候,也頻頻問起他的家人北地之事。
白九規規矩矩坐在對面,問什麼,答什麼。
另一邊,書局。
謝正陪黃明遊先生在付書稿,書局裡的人起初並不重視,後來黃先生發了好大脾氣,書局的總編才急匆匆趕下來,親自接待,那個小辦事員站在一旁鵪鶉一樣,聽說“黃明遊”三字,臉瞬間就嚇白了。
黃先生在書局親自整理了一上午的書冊,付印製,弄好之後才走出來,邊走邊錘腰側,搖頭笑道︰“年紀大嘍,當初跟著商隊走南闖北也不見這麼許多『』病,現在不過是坐兩日船,再忙上半天,這老腰就疼得厲害。”
謝道︰“先生做事太趕了,注文本就繁瑣,您又和章教授合繪了江河圖,這些圖旁人繪上十天半個月都未必能出一張,應該慢些來。”
黃先生笑道︰“不行呀,還有那麼多學生著,總要趕在春天前書定下。”
謝驚訝︰“給學生?”
黃先生點頭應道︰“是啊,我同北平那幾位商議過,大家夥兒一致同意盡快印出來,不止這一卷,後面還有一整套呢。我這些年跟著商隊走南闖北見過許多山川河流,因此負責這一卷,其余書卷由北平大學眾位教授傾力合作,從小學到高中都有,我華國萬萬裡土地上大好山河,應當讓學生們都記住。”
黃先生年紀大了,兩鬢白發,謝當初見到他的時候相比能看出額前皺紋增多。黃先生上的傲骨依舊,不管多大年紀,即便背著手走路,也直了脊背。
謝看著他慢慢踱步,哼著小曲走下樓去的影,不止為何忽然想起先生乘船而上的模樣。
老先生手撐在船欄桿上,仰頭看著逆流而上的道道青山峰巒,眼中帶了自豪。
這份自豪來自於他眼中的山川河流,來自於他腳下的土地,也來自於他腦海中讀背誦的千萬卷書籍——那是他心中的故土,是他的國。
猜你喜歡
-
完結331 章
我爸是大佬帶球跑的小嬌妻
身为男男生子世界云家不受宠亲儿子池谨轩的拖油瓶,池映秋的日常就是看着那个万人迷云家养子云丛熹现场表演绿箭。 作为一个年仅三岁的拖油瓶,池映秋扁了扁嘴强忍委屈,啪叽一声当众摔倒在养子面前:“宝宝不痛,不是小叔叔推的宝宝,宝宝知道错了。” 养子:??? 亲爹:??? 云家老太爷云仲天淡淡扫了一眼云丛熹:“我知道你讨厌谨轩,但你何必要对一个孩子撒气?” 亲爹:也不知道你另一个爹是什么狗脾气,才能让我生出你这种天生小白莲。 池映秋:我知道,他刚刚想要和你联姻但是被你拒绝了。
72.4萬字8 11663 -
完結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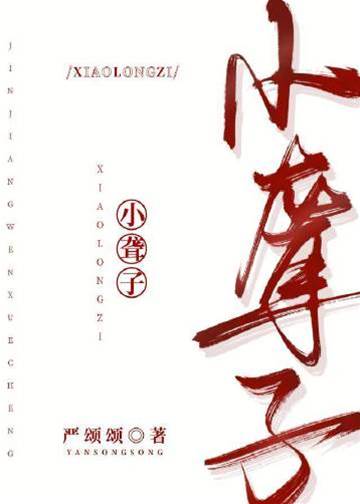
小聾子受決定擺爛任寵
憑一己之力把狗血虐文走成瑪麗蘇甜寵的霸總攻X聽不見就當沒發生活一天算一天小聾子受紀阮穿進一本古早狗血虐文里,成了和攻協議結婚被虐身虐心八百遍的小可憐受。他檢查了下自己——聽障,體弱多病,還無家可歸。很好,紀阮靠回病床,不舒服,躺會兒再說。一…
30萬字8.18 1763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