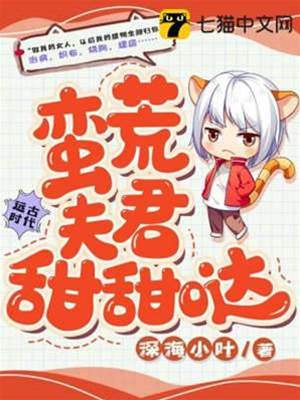《明朝好丈夫》 第58章 皇帝老子不是好人
青磚石上已滴淌了一灘的,劉公公如篩糠,仍舊一次次的用腦袋重重磕著頭,發出咚咚的聲響。
不知過了多久,老太監終於擱下了筆,用著渾濁的眸子掃視了劉公公一眼,卻是如沐春風地道:“茶……”
站在老太監邊的小太監弓著子去斟茶了。
“廠公……我……我……”劉公公整個人已經虛,擡起臉時,整張臉鮮淋漓,恐怖到了極點。
老太監嘆了口氣,靠在椅上微微笑道:“雜家是怎麼說的?要拿回煙花衚衕,你當時聽到了嗎?”
“聽……聽到了……”劉公公膽戰心驚地道。
老太監冷笑道:“你沒有聽到,你是在奉違,雜家問你,煙花衚衕現在在誰家的手裡?”
“當時聽說太子殿下……”
砰……
老太監笑得更冷,拍案打斷了劉公公的解釋:“雜家要的是煙花衚衕的份子錢,你說再多也是狡辯!”他目一收,凌厲的氣勢瞬間不見,一副懶洋洋的樣子靠在椅後的墊上,乾枯的手了太,慢吞吞地道:“牟斌那邊,不必再管了。他是個聰明人,這個時候肯站出來魚死網破,咱們沒有必要陪他一道碎骨。事鬧大了,不但讓人笑話,閣那邊也有了把柄說辭,到時候沒準兒會有人說出什麼是非來。把咱們東廠的人都收回來,他們暫時不要輕舉妄,與錦衛的爭執暫時放一放。”
“是。”雖是這麼說,但劉公公心裡還是不甘,若是東廠這邊示弱,這煙花衚衕只怕再也收不回了。他這時腦子已是昏昏沉沉的,腦門上還泊泊地滲出來,順著他的鼻尖、下滴淌下去。
這時候那小太監已經端了一杯熱茶來,老太監慢悠悠地接住,揭開茶蓋好整以暇的吹著茶沫,漫不經心地道:“問題的癥結不在錦衛,也不在牟斌,而是在那個姓柳的百戶上。你方纔說太子殿下這幾日都與他走得近,還拜了師?”
Advertisement
“沒錯,姓柳的那邊,小人已人死死地盯著,這幾日太子殿下每日都去百戶所與他呆在一起,好像是說學什麼拳腳,鬧得很不像話。”
見廠公消了氣,劉公公才放下了心,恢復了神智,對答如流起來。
“還有一樣,聽說那姓柳的還時常與太子切磋武藝,對太子爺拳腳,太子每次回東宮的時候都是傷痕累累。除此之外,還說要讓太子做什麼幫閒……”
老太監一不地聽劉公公的絮叨,待劉公公說完了,便喝了一口茶,眼中掠過一殺機,道:“這麼說來,這個姓柳的是再不能留了,就算不爲煙花衚衕,有他在一日,早晚要爲禍,若是攀附了太子,你我遲早要人頭落地。”
劉公公擡起頭,驚訝地道:“廠公的意思是人手?”
老太監微微一笑,譏諷地看了劉公公一眼,道:“他是欽賜的百戶,你說這些話未免太大逆不道了。解鈴還需繫鈴人,要手的不是東廠,而是皇上。你先查清楚太子與柳乘風來往的規律,等什麼時候皇上有了閒雅緻,再請皇上出宮一趟。”
劉公公爲難地道:“皇上日理萬機,未必肯出宮去。”
“這也未必。”老太監冷笑一聲,慢吞吞地喝了口茶,繼續道:“若是關係到了太子,就大大不同了。”
劉公公恍然大悟,連忙道:“我明白了,這是借刀殺人,皇上新近誇獎了柳乘風,要除掉那姓柳的,也只有皇上才,只要讓皇上看到姓柳的諂太子,到時龍大怒,誰也救不了他。”
老太監嘆了口氣,道:“劉,你別的地方都好,有忠心、也肯辦事,就是腦子裡缺了一弦,許多事不是喊打喊殺就能辦的,大道走不通,就走小路,只要能把事辦,總會有辦法。你額頭上的傷怎麼樣?”
Advertisement
劉公公一副寵若驚的樣子,連忙道:“廠公,不打的,是小人該死,不會辦事,差點毀了廠公的清譽,令廠公讓人恥笑,從此以後一定悉聽廠公教誨,凡事多用腦子。”
老太監頜首點頭,臉平淡地道:“好,很好,也不枉雜家疼你一場,湖州鎮守太監周勇送來了一些稀奇的玩意,待會兒你去挑幾個好的去玩玩吧。”
劉連說不敢。
老太監道:“這有什麼敢不敢的?這是雜家賞你的,下去吧。”
劉一副激涕零的樣子退了出去。
老太監吁了口氣,眼中掠過一冷意,目注視著桌上冉冉的宮燈,隨即將目闔起來,淡淡道:“這狗東西,真是越來越不會辦事了。”
一邊的小太監微微一笑,諂地朝老太監笑了笑,道:“乾爹,這宮裡肯辦事的多了去了,劉既然惹得乾爹不高興,就索把他分派到針工局去,這樣的廢,留著有什麼用?”
老太監擡眸看了小太監一眼,冷冷一笑道:“怎麼?你就這麼急不可待要將劉取而代之嗎?”
小太監不由打了個冷戰,忙道:“兒子不敢。”
老太監換上笑容,道:“你有這個心思也未必是壞,咱們都是沒了的人,若是連這點兒野心都沒了,活著還有個什麼意思?不過劉還要留著,他雖然愚鈍,卻總還算勤懇,只要這一趟除掉了姓柳的,也算是他將功贖罪了。”
老太監說罷,便沉默下去,又撿起桌上的奏書翻閱,專注到忘了邊小太監的存在。
………………
柳乘風的日子過得平淡無奇,每日除了值堂,偶爾也會去王鰲府上一趟,王鰲的痔瘡已經進了第二個療程,病明顯緩和了不,爲柳乘風的恩師,自然免不得要教誨柳乘風幾句,柳乘風反過頭去,便將王鰲的教導返還給朱厚照。
Advertisement
朱厚照每日都興致地到百戶所,對這個頑劣的太子來說,柳乘風越是折騰他,這神功才越厲害,若是絕世武功唾手可得,那還什麼絕世神功?幾天的功夫,柳乘風已經讓他抄了四遍論語,原先那如狗爬的行書如今總算有了幾分模樣,進步很明顯。
到了後來,柳乘風在百戶所裡閒著沒事便讓朱厚照背誦論語,朱厚照咬著牙誦讀記憶,好在這論語字數不多,還不至於把朱厚照難倒,朱厚照本就是個極聰明的人,只要用了心,雖然未必能倒背如流,卻也不至於有太多的誤差。
“師父,磨礪心志還要多久?什麼時候可以開始練皮煉骨?”
朱厚照漸漸和柳乘風稔了,隔三差五總要問一遍這問題才肯罷休。
“不急,不急,好徒兒,這練功就像建房一樣,地基打得牢,房子纔好。現在師父讓你築基,便是讓你打好基礎,將來練起功來才能事半功倍。”
柳乘風每次都只能這樣回答,事實上,真要讓柳乘風教朱厚照學武功,柳乘風也是不會,現在拿了人家的手短,想把這傢伙逐出門牆都沒有藉口,只好能拖延幾日算幾日,反正讓這傢伙讀讀書也不是什麼壞事,總歸對得起那一千斤臘的學費。
不過那拜師的六禮,也讓柳乘風賺了個鉢滿盆滿,他將這些東西全部送出去,各家也都送了回禮來,有字畫有瓷瓶有金銀首飾有綢布匹,滿打滿算下來,折銀居然賺了兩千多兩,更有意思的是那陳泓宇,送他十斤臘,總共也不過百文銀子的東西,人家是回了一個上好的青花瓷瓶來,柳乘風頗知道一些識別古玩的技巧,只一看便知道這瓷瓶兒的價值在紋銀三十兩以上。
這一筆財富,可是朱厚照這徒兒給柳乘風賺來的,柳乘風決心對朱厚照好一些。所以有時候他閒來無事就會過問朱厚照的功課,也會他坐在一邊閒聊。
“師父,那郭靖這麼蠢,也能學到絕世武功?”
“南帝真是個呆子,好好的皇帝不做,偏偏要去做和尚。”
柳乘風和朱厚照的關係已是親近了許多,聽到朱厚照對他的‘故事’大發議論,不吹鬍子瞪眼道:“你懂什麼,並不是每個人都做皇帝的。”
朱厚照想了想,道:“這個倒是,就比如說我父……比如說當今皇上,日夜在宮裡理政務,看上去坐擁天下,擁有四海,可是頭髮都熬白了,真是可憐。”
柳乘風冷笑,很世故地道:“皇帝老子在宮裡,你如何知道他是日理萬機,還是在與三千佳麗周旋,臥醉在溫鄉里?”
柳乘風這句話有些大逆不道,不過畢竟這裡沒有外人,他不屬於這個世界,所以對任何事都抱有一種懷疑態度,說出這番話倒也不覺得什麼。
猜你喜歡
-
完結108 章
穿越亂世醫女
醫科大學研究生文丹溪穿越到一個類似明末的亂世,遇到集二、?、萌於一身的土匪頭子陳信。世人皆以爲他是狼,她是羊,卻不知,她才是一隻披著羊皮的狼。這是一個腹黑女與二貨男的鬥智史。
35.7萬字8.18 41121 -
完結66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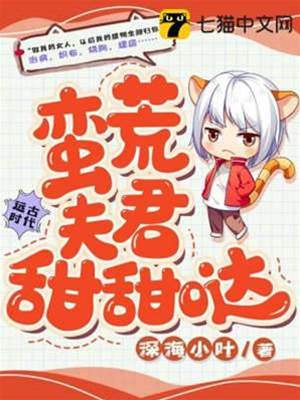
蠻荒夫君甜甜噠
薛瑤一覺醒來竟穿越到了遠古時代,面前還有一群穿著獸皮的原始人想要偷她! 還好有個帥野人突然出來救了她,還要把她帶回家。 帥野人:“做我的女人,以后我的獵物全部歸你!” 薛瑤:“……”她能拒絕嗎? 本以為原始生活會很凄涼,沒想到野人老公每天都對她寵寵寵! 治病,織布,燒陶,建房…… 薛瑤不但收獲了一個帥氣的野人老公,一不小心還創造了原始部落的新文明。
117.6萬字8 38714 -
完結640 章

王妃音動天下
想催眠別人,卻被人反催眠,難道帥哥天生對催眠術有免疫力? 但是,催眠後這是個啥情況? 穿越還是做夢,爲啥這個帥哥變成了王爺? 孟漓禾:大哥妳是誰?我是不是在做夢? 宇文澈:今日妳我大婚,妳說本王是誰? 不過,這壹群腦洞突破天際的下人們都是什麽鬼? 誰能告訴她這是怎樣壹個崩壞的世界啊! 請允許我狗帶!...
169.1萬字8.18 37422 -
完結493 章

一覺醒來本妃失寵了
一覺醒來,蕭清然失去記憶,老了十歲,從新嫁娘變成倆娃的娘,還在和王爺夫君鬧離婚!老公,孩子,王妃之位,十年后的自己,說不要就不要了?!蕭清然兩眼一黑,在寧抉和離書都給她寫好時,一屁股坐在男人大腿上,環住他脖子,目光真摯明亮,聲音嫵媚:“夫君…
78.9萬字8 57136 -
完結889 章

謀御江山
莫笑人間少年夢,誰不少年夢皇朝,談笑風云,羽扇綸巾,少年白衣,絕代傾城……
150.9萬字8 1574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