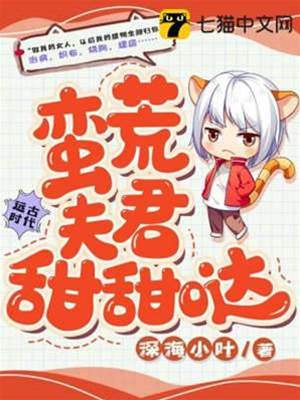《明朝好丈夫》 第964章 離心離德
其實在這大明朝的蕓蕓衆生之中無非就是兩類人,一種是知道的人,另外一種是不知道的人,前者嗅覺靈敏,稍微風吹草都能看出和端倪,後者渾渾噩噩,而現在柳乘風絕對相信,京師的那些明眼人絕對都看出了貓膩。
可最大的問題就在於,這麼多人能看出貓膩,爲何所有人都沉默。
這是一件很嚴重的政治問題,把皇上比作秦伯其心可誅,可是偏偏,上到閣下到使竟是沒有一人跳出來,就彷彿什麼都沒有看見,什麼都沒有聽見,都了瞎子聾子。
絕不可能,唯一的解釋只有一個,有人樂見此事。
許多事一旦剝繭出了本來的面目,就很不簡單了,柳乘風沒有什麼聲,他決心再等等看,不過他的心思剛剛生出來,焦芳就已經上門了。
這些時日焦芳上門比較勤快,隔三差五總要來,生怕自己和柳乘風還不夠稔一樣,他的臉鬱,見了柳乘風連禮儀都顧不上了,直接問道:“殿下可留意了坊間的議論嗎?”
這句話簡直就是空話,柳乘風是什麼出的,若說沒留意那就是騙人。
柳乘風點點頭,道:“倒是留意了一些。”
焦芳急道:“這些人真是膽大包天,殿下需小心提防啊,若只是有一些膽大包天之徒胡言語也就罷了,可是整個朝野上下非但無人制止,反而是愈演愈烈,若說這背後無人指使慫恿,下一萬個不信,只怕在這廟堂之上,有人包藏禍心,早就做起迎聖的夢了。”
柳乘風今日對焦芳的態度好了許多。
不管焦芳的品行如何,至在這時候焦芳是站在自己一邊的,這就足夠了。焦芳需要自己支持。而自己也需要當今皇上,二人的利益一致。柳乘風手,道:“你先坐下說話。”
Advertisement
焦芳點了點頭,道:“還有,下有個門生在禮部衙門裡公幹,昨天夜裡他來和下說,莫說是在坊間,便是在禮部值堂裡。也有人議論此事,非但沒有上制止,甚至連回避的意思都沒有,如此看來,這定是有人搗鬼了。哎……這些人真是已經急不可待了,我還聽說。聽說安陸那邊,似乎也有人不太安份。”
安陸是個很不起眼的地方,可是卻有個了不起的人,那便是先帝的兄弟興獻王朱佑阮,朱佑阮算是一個比較悲催的人,化皇帝獨寵萬貴妃,只生了朱佑樘和朱佑阮二子,在萬貴妃的威之下,這二人都是膽戰心驚。每日都生活在惶恐之中。
可是不管怎麼說,爲長子的朱佑樘運氣還是不錯的,等到化皇帝駕崩,好歹也做了皇帝,雖然他這皇帝苦了一些,畢竟還是九五之尊。朱佑阮就沒有這麼幸運了,他被封去了安陸,安陸是什麼地方?那兒放在整個大明都極不起眼,天下富庶的地方多的是。而安陸怎麼看都排不上字號。也由此可見,這位化皇帝的嫡親脈在化眼裡的地位如何?
吃了半輩子苦。爲天潢貴胄,後半輩子多半也只能在窮山裡度過,朱佑阮心裡頭想必很不痛快。
只不過痛快不痛快都和他無關,朝廷的法在這裡,你還想翻天不,只是現在,這位不太起眼的藩王如今似乎變得有些炙手可熱,至在京師裡有些人蠢蠢,而朱佑阮似乎也有點兒想要遙相呼應的意思。
畢竟他是先帝的嫡親兄弟,按輩分來說,也是當今皇上關係最親近的叔父,假若當真到了某個時候,按照禮法,朱佑阮苦盡甘來似乎是可期的事。
Advertisement
柳乘風不由皺眉,這些時日他過於關注去尋找皇帝,卻是差點疏忽了這位原本不可能和自己有什麼集的藩王,這個人給柳乘風的直覺很危險。
柳乘風道:“興獻王本王所知不多,此人如何?”
焦芳很簡練的回答道:“勤學而素有威儀。”
這分明是誇獎的話,可是在柳乘風耳朵裡聽來,卻冷笑起來:“誰知道是不是沽名釣譽,又或者是有人在背後造勢。”
焦芳深以爲然的笑笑,道:“殿下明察秋毫,令人佩服。”
柳乘風吁了口氣,道:“說這些虛的,這幾日你在閣,更要留心一些吧,本王現在作壁上觀,且要看看到底是什麼人要玩花樣。”
焦芳點頭,道:“說起來時候已經不早,下就不叨擾殿下了,閣那邊,還有事要置,告辭。”
柳乘風今日出奇的將焦芳送了出去,讓焦芳有些寵若驚,焦芳知道,自己終於算是真正的楚黨,至楚王殿下已經默默認可。
他出了楚王府,隨即乘轎進宮了閣,閣這邊近來沒什麼大事,皇上總之沒有音訊,一開始大家還有些不方便,可以漸漸也就習慣,大家各自管顧自己的事,倒也沒有什麼子。
甚至沒有了一些東西的束手縛腳,有人覺得,這也未嘗沒有什麼不好,至多了幾分隨心所。
當然,這種心思誰都不敢說出。
焦芳到了自己的案牘之後坐好,見李東和楊廷和二人湊在一起低聲商議著什麼,他豎著耳朵,聽到一些隻言片語,似乎二人討論的是調度蒙古衛所的事,焦芳角溢出了一冷笑,按著案牘突然道:“兵部上呈來的編練蒙古各衛的奏書,二公看了嗎?”
Advertisement
楊廷和擡眸,厭惡的看了焦芳一眼,正道:“看是看了,不過有些不妥之。”
“哦?老夫倒是覺得沒什麼差錯,不知哪裡有不妥,還請楊公請教。”焦芳道。
楊廷和倒也不藏著掖著,道:“問題的關鍵在於各衛替衛戍各方,這麼做未免糜費太大,軍馬每隔三年調一次,所需的消耗可是不小。”
焦芳不痛不的道:“替調,這是爲了加強對蒙古各衛的控制,只有他們居無定所,才能保障他們不會鬧出子。”
“話是這麼說。”李東突然口,道:“可是替去廉州,未免遠了一些,況且廉州是藩國,豈有讓大明國庫供養藩國替駐軍的道理?”
焦芳警惕起來,其實許多驚天地的事,都是在一件小的不能再小的事上發,這便是導火線,對方的意圖,似乎就是想在楚王與蒙古人的和議裡做點文章,焦芳道:“這一次擊敗蒙古鐵騎的,是楚王殿下,楚王殿下居功至偉,況且楚國也不是尋常的藩國,它與大明本爲一,又何必要分出彼此來?”
楊廷和輕笑,道:“這可不對,楚國是藩國,藩國就是藩國,你說大明與楚國是一,那麼軍政不能統一?既然軍政都不統一,那麼這一就是個笑話,大明是天朝,楚國爲藩,楚王殿下也是藩王,藩王立了功,天朝自有賞賜,可是焦公豈能混淆了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我大明雖然恩澤四方,可是禮法不可輕廢,何謂禮,又何謂法?所謂禮法,無非是上下等級分明,任何人做好自己的事而已,在其位謀其政嘛。”
焦芳心裡冷笑,他這種老江湖若是連這句話的意思聽不出那就算是白混了,人家說在其位謀其政,其實就是諷刺楚王,說楚王既然是藩王,現在卻是管起天朝的事務,獨攬天朝的兵權,這不就是狗拿耗子?另一層意思又是講清天朝和藩國的區別,既然有區別,那麼藩王就是藩王,藩王有自己該做的事……
若是在一個月前,在京師七八糟,在烽火四起的時候,楊廷和說起這番話倒也沒什麼,可是當時柳乘風來京的時候,楊廷和這些人卻是坐其的人,等所有的事都解決了,現在又覺得柳乘風在這裡礙事,想讓楚王滾蛋,這如意算盤,倒是打的啪啪作響。
狡兔死走狗烹,這可不只是發生在皇帝和臣子之間,現在這閣大學士又何嘗抱著這個心態,無論他們自認爲自己的立場如何正當,可是手法上來說,還真有些小人。
焦芳不聲,淡淡的道:“許多事說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凡事都有例外,大明和楚國就是如此,先帝在的時候,曾言楚國乃一之國,楊公難道連先帝的言說也要推翻?這是先帝的意思,便是當今皇上在這裡,也不會反對這件事,依老夫看,兵部的奏書和章程並沒有什麼不妥,若是楊公有異議,大不了請太后聖裁便是。”
焦芳倒也聰明,他沒有說把事在閣部解決,因爲在閣裡他不佔優勢,也沒有說在朝廷部解決,因爲朝廷部全是對方的人,焦芳是孤掌難鳴,所以他才提請太后聖裁,太后終歸心裡還是偏向楚王這邊的。
……………………………
有點晚有個朋友來竄門,耽誤了,抱歉。
猜你喜歡
-
完結171 章
一世紅妝
林慕夕一夜之間穿越到一個叫做青木的小國家。她成爲了林府的娣長女。可是她這個大小姐做的真是憋屈,不但父親不疼,還從小失去了母親。在家裡常年遭受弟妹的欺侮。可是現在的林慕夕已經不是以前的那個懦弱的林慕夕。她可是從現代來的百富美。不但知識淵博,還身懷各種技能,怎麼可能繼續任人宰割?於是,林府開始雞飛狗跳。林慕夕一個
50.4萬字8 26193 -
完結2105 章
重生醫妃
天才醫學博士穿越成楚王棄妃,剛來就遇上重癥傷者,她秉持醫德去救治,卻差點被打下冤獄。太上皇病危,她設法救治,被那可恨的毒王誤會斥責,莫非真的是好人難做?這男人整日給她使絆子就算了,最不可忍的是他竟還要娶側妃來惡心她!毒王冷冽道“你何德何能讓本王恨你?本王隻是憎惡你,見你一眼都覺得惡心。”元卿淩笑容可掬地道“我又何嘗不嫌棄王爺呢?隻是大家都是斯文人,不想撕破臉罷了。”毒王嗤笑道“你別以為懷了本王的孩子,本王就會認你這個王妃,喝下這碗藥,本王與你一刀兩斷,別妨礙本王娶褚家二小姐。”元卿淩眉眼彎彎繼續道“王爺真愛說笑,您有您娶,我有我帶著孩子再嫁,誰都不妨礙誰,到時候擺下滿月酒,還請王爺過來喝杯水酒。”
355.2萬字8 194934 -
完結66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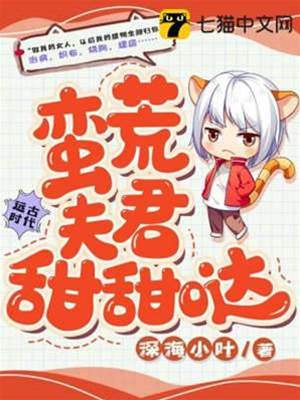
蠻荒夫君甜甜噠
薛瑤一覺醒來竟穿越到了遠古時代,面前還有一群穿著獸皮的原始人想要偷她! 還好有個帥野人突然出來救了她,還要把她帶回家。 帥野人:“做我的女人,以后我的獵物全部歸你!” 薛瑤:“……”她能拒絕嗎? 本以為原始生活會很凄涼,沒想到野人老公每天都對她寵寵寵! 治病,織布,燒陶,建房…… 薛瑤不但收獲了一個帥氣的野人老公,一不小心還創造了原始部落的新文明。
117.6萬字8 38714 -
完結759 章
神醫棄女要強嫁
明幼卿是中西醫雙料博士,一朝穿越,成為被太子退婚後,發配給了廢物王爺的廢材嫡女。 世人都笑,廢材醜女配廢物王爺,真絕配。 只是新婚後……某王:沒想到明家醜女樣貌傾城,才氣絕倫,騙人的本事更是出眾。 某女勾勾手:彼此彼此,也沒想到廢物王爺舉世無雙,恩,身材也不錯~兩人真真絕配!
138.2萬字8 11055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