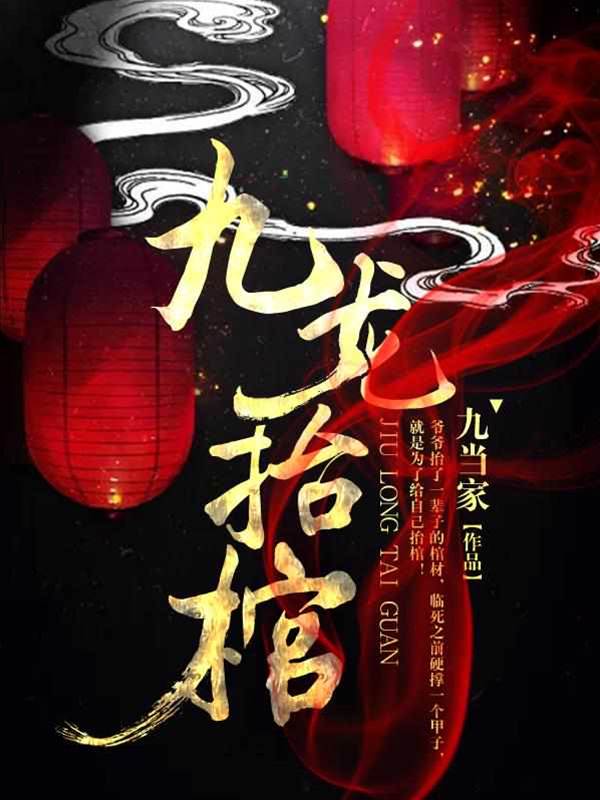《喪屍危機末日》 第10章 談話,計劃(下)
“哦!”安傑與那個人恍然大悟。
“我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才真正的確認了他們都是犯人,他們鉗制住我和安傑時所用的那種技巧,他們,應該都是有練過的吧,或者說,他們都是有一定的訓練底子……”張鬱說話的速度漸漸地慢了下來,眼神冰冷警惕地盯著人。
“嗯,這些人以前都是有學過武,以那個陸仁甲的話來說就是,他們都是他最最信任的夥伴,能在怪的手中活下來的夥伴!”人重重地點頭。
“嗯。”張鬱冷冷地盯著人,“那你有什麼要和我們說的嗎?如果就是這些我們早就知道的訊息,那麼,我們就無話可說了……況且了,就算你跟我們說了這些,那對於我們有什麼幫助?”張鬱無奈地擺了擺手。
“如果沒有別的事的話,那我們就回去了。”安傑稍稍明白了張鬱的意思,也看向了那個人,等待著的下文。
“你們,不害怕他們嗎?”人不回答張鬱的問題,突然地就問了這麼一句。
“害怕?爲什麼要害怕?他們比喪更可怕嗎?”張鬱徑直說道。說完,他還看向了安傑……的口袋。
那裡面可是還放著一把槍啊!
他們躲得過槍嗎?
“你們還不知道呢……”人搖了搖頭,緩緩地說道:“他們可都是殺人犯啊,其中那個做陸仁甲的男人,他的上可是揹負著十多條人命啊,早就被國家判了死刑的這麼一個男人。”
“剩下的也都是一些做著一些殺人放火,搶劫強勾當,被國家判了死刑的傢伙,這麼危險的傢伙,你們應該要好好地躲開他們!”人冷冷地看著二人。
“嘿。”張鬱冷笑,“現在可是什麼時候啊,士,你應該也是瞭解的吧,一隻只喪如同雨後春筍一般不停冒出,而且它們的來源就是我們人類。現在可還沒有研製出對抗這些喪瘟疫的疫苗,用不了多久,整個世界就會和小說中所寫的一樣……”
Advertisement
“到都是燒殺掠奪,強殺人更是如同家常便飯一般,爲了一口吃的食,男人可以跪下黃金膝,人則可以不用立牌坊了,爲了活著,出賣又算得了什麼?”說著,張鬱還戲謔地看向了。
“你不也是知道世界今後的格局,才這般呆在他們邊的嗎,當他們行軍途中的一個安婦……”
啪!
張鬱的餘音還沒有落下,人一個掌就甩在了張鬱的臉上,的眼眶中似乎有淚花在不停地打轉著。
“對,對不起……”看著那個楚楚可憐的樣,張鬱低下了頭吶吶道。
“沒關係,你說對了,我就是他們行軍途中的一個安婦。”人了眼角,淡淡地說。
“你們,想不想活下去?”人的眼神又恢復了冰冷。
“嗯。”安傑點了點頭,完了還拉著張鬱一同點頭。
“那些傢伙衝不出這裡,下著雨,外邊又是漆黑的一片,如同螞蟻般多的喪怪遊在外面,我跟你們說一個的數字,外邊的喪數量已經超過了五千,包括整個MN軍區的民兵、犯人以及在發電廠中工作的工人,他們大部分都沒有來得及跑掉,都被喪啃咬中了,都變了喪。”
“這些傢伙自然也是知道這點的,於是我騙他們說可以開這裡的車衝出去,他們就帶著我來到了這裡,但是他們找不到發車的鑰匙,可是我卻是知道鑰匙被放在哪裡的。”說到這,人朝著他們眨了眨眼睛。
“聽著,等下你們就帶著你們的人離開這裡吧,可能會有些麻煩,但是憑著你們的智慧應該可以逃得出這裡,然後去到鑰匙擺放的地方,取得鑰匙然後再回來,聽好了,鑰匙就是放在……”
Advertisement
“你想和他們同歸於盡嗎?”不待說出鑰匙的擺放地,張鬱突然就開口打斷了的話。
人愣住了,完全沒有反應過來,呆了片刻,才了眼角。
半晌,才吶吶道:“你們真的是很聰明呢,這也看得出來,讓我對你們的期待又加大了一分……”
“我已經不是一個清白的人了,這些混蛋,他們將我堅守了二十五年,只留給最男人的那道貞給捅破了,我怨恨他們。所以,我要和他們一起下到地獄去,帶著他們去見我將來的人……”人咬著牙面寒地說著。
一邊說,還一邊咬了咬脣,直到脣流下了猩紅的跡才鬆開牙齒。
“所以,你們的人留在這裡是很危險的,他們也會對們做出,和對我做出的事一樣,你們不想後悔吧,那就和你們的人一起活下去!”人苦笑著,笑容中有一的悲哀。
“其實……”安傑開口了,“們只是我們的老師還有同學而已,而那位老師是他的姐姐,所以並沒有存在人還有人的說法。”
“哦?”人調皮地眨了眨眼睛,半響才笑道:“們兩人對你們的很不一般哦,我可以看得出來。”
“事實上,你其實不需要那麼做的……”張鬱看著說。
人也看向了他,黑暗之中看不清的臉部表。
“我已經在算計他們了,我知道我們是沒有辦法和他們拼的了,我們的上幾乎是沒有任何的危險了。所以我最後才說出要把附近的況查看清楚,我的目的是想要讓他們去查看,因爲我們只是一些可憐兮兮的逃命學生而已,他們爲了繼續僞裝下去是絕對不會讓我們去查看的……”張鬱淡淡地說。
Advertisement
“你怎麼知道,還是說你有什麼把握?”人問。
“最開始的時候那個傢伙不是說過嗎,他們並不是什麼危險的人,他之所以這麼說,是他們因爲還畏懼著警察,準確的說是害怕死亡,你是這麼說過的吧,他們都是死刑犯,他們也很清楚被警察抓到了的最終結果。他害怕我們知道了他們的份之後要告訴警察或是軍人,所以他纔對著我們裝出友善的一面。”張鬱繼續說。
“當然了,爲了避免意外的出現他們也可以殺了我們滅口,但是現在我們都是同一條繩子上的螞蚱,與其殺掉了可能對他們逃出喪堆有用的人才,倒不如好好地利用一下。所以他們才問我們是如何逃出學校的。”
說到這,張鬱冷笑了起來,“那些白癡估計是想測試一下我們對於他們的利用價值,才問出那個問題的,所以我才老實地回答,我們之中各個人的能力幾乎都沒有瞞地告訴了他們,我這麼做完全是爲了讓他們瞭解到我們的利用價值,以目前的況來看,我是功了的。”
接著,張鬱繼續說道:“他們知道了我們可以利用的一面,但是他們還是想確認一下我們的利用價值到底還有多大,所以又問我他們今後該怎麼辦,但我也是完完全全地把我的想法告訴了他們,那些白癡應該是心了的,至我看起來是這樣。”
頓了頓,張鬱接著說:“我一開始也說得很清楚了,我們只是一羣手無縛之力的學生,我說的計劃已經打他們的心了,換句話說,我對於他們這個團有著智囊一般的貢獻,知道二十一世紀最缺的是什麼嗎,那就是人才啊,特別是像我這樣腦袋發達的稀人才。”
“如果他們讓我們去查看況,那在他們的潛意識中我們絕對就是有死無生的了,但是我對他們還有利用價值啊!與其讓一羣手無縛之力的人才去查看況死掉,倒不如讓他那些強大又信任的夥伴去查看況,對於這整個團也都有所作用。”張鬱推了推鼻樑骨。
“所以,我才這麼的有把握……至,在逃出這個部隊駐地之前,他們不會對我們做出任何事。”張鬱盯著說。
“那麼如此一來,只要把查看況的人全都支到喪的集中地附近,然後再給他們下一些絆子,既可以把犯人們全都合合理地推到喪堆裡,而我們這邊還是佔著道德的制高點,開的藉口那也是很簡單的,一句判斷失誤就可以了,就算他事後想要找我們的麻煩,那對我們也是沒有了任何的威脅……”張鬱冷冷地說著,說完,他又看向了安傑……的口袋。
一把槍還臥在裡面呢!
(厲害,真的是很厲害!)
安傑幾乎是像聽著天書一般的,張鬱這個小子在地算計他們,如果不是他親口說出來,安傑恐怕還不知道呢。但是相反的,他又有些同那些匪徒了,所謂的被賣了還幫著數錢就是這麼一回事了
張鬱擺了擺手,無奈地繼續說道:“你剛剛的那個計劃啊,在我的眼裡幾乎是沒有功地可能了。首先,你怎樣讓我們去尋找那個車鑰匙?就算你告訴了我們車鑰匙的所在,但是我們連走出這個車庫的可能都沒有,該怎麼去尋找那個車鑰匙?”
“他們已經知道了我們的利用價值,除非將我們的剩餘價值全都榨完畢後,他們是不會把我們放走的了,所以一開始把我們的東西全都搜刮走就是這麼一回事了,如果我們真的沒有什麼利用價值,他們要把我們直接殺了,或是當作吸引喪的炮灰也不是不可能。”
頓了頓,張鬱接著說:“所以我說,你這個計劃完全沒有功的可能,還是好好聽我的吧,明天將這些混蛋全都殺死後,我們就一起活下去!”張鬱笑了,笑得像花一樣燦爛。
“你……你真的只是普通的高中生?”人有些不敢相信,不相信這種計劃會是從一個小孩子的口中說出來的,甚至都沒有到這個小孩子的冷,只是訝異著他的智慧。
“呵呵,爲了活下去,我什麼都願意去做,如果你不是突然拉著我們出來了,我可能還會給你設一個局,讓你死於不明不白之間。”張鬱冷冷地看著人笑著說。
人不住這道寒冷的目,忍不住地打了一個寒,眼前的這個年,不,他的智慧足以用妖來形容了,應該稱爲怪纔對,毫沒有懷疑他這句話的真假。
“哈哈,騙你的啦,我們只是一些普通的高中生,這只是我瞎掰的,請姐姐不要在意哈!”張鬱一改剛剛的冰冷,嬉皮笑臉地說著。
“……”人完全沒有反應過來,眼前這個嬉皮笑臉的小子,還是剛剛那個說要殺了的人嗎。
“呵呵!”
終於,人的臉舒緩了過來,僵的臉終於是浮起了燦爛的笑容,“我明白了,那就期待你明天的表現吧,替我把這羣人渣都給殺了吧!”
…
猜你喜歡
-
完結1126 章

茅山後裔
我是一個"災星",剛出生就剋死了奶奶,爺爺以前是個道士,爲我逆天改命,卻在我二十歲生日那天離奇死亡.臨死前,他將一本名爲《登真隱訣》的小黃書交給了我,卻讓我四年後才能打開…
291.7萬字8.18 37384 -
完結314 章
詭案手冊
我叫方怵,五年前畢業於首都人民公安大學犯罪學學院,從警五年,我一直處在刑偵第一線,經歷了無數個不眠夜,也親手逮捕了數不勝數的變態兇殺犯。 在我所經歷過的案件之中,案發現場千奇百怪,人們口中所說的偽靈異事件更是數不勝數,一個只有五歲的小男孩,被兇手扒皮抽筋,製作成人皮竹籤,我也親眼目睹了一個活生生的人在我眼皮子底下變成一灘血水,誰又能想像,有些民間科學狂人,盡會妄想將人腦移植到電腦上,繼而通過腦電波實現長生不老的瘋狂想法。 噓,也許下一個被害者就是你,你,準備好了嗎?
150.3萬字8 6707 -
連載138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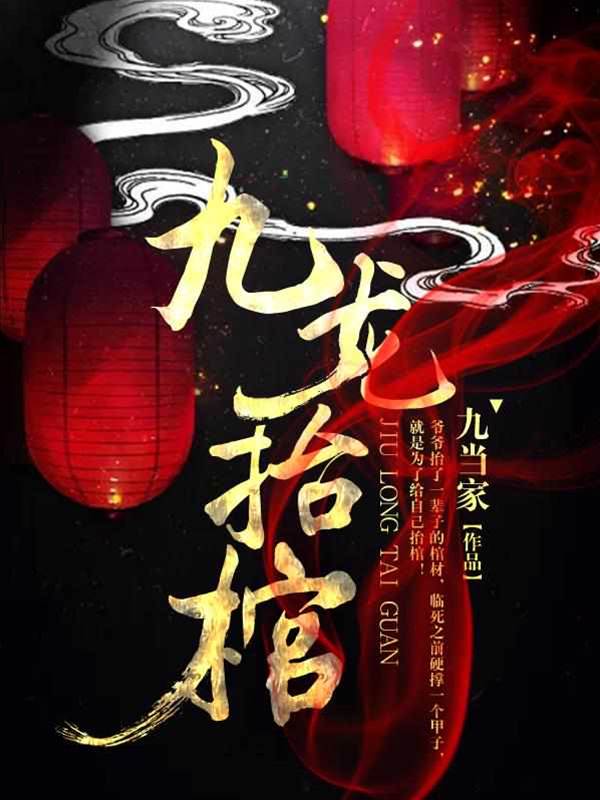
我是一名抬棺匠
爺爺出殯那晚,我抬著石碑在前引路,不敢回頭看,因為身后抬棺的是八只惡鬼……
272.9萬字8.46 245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