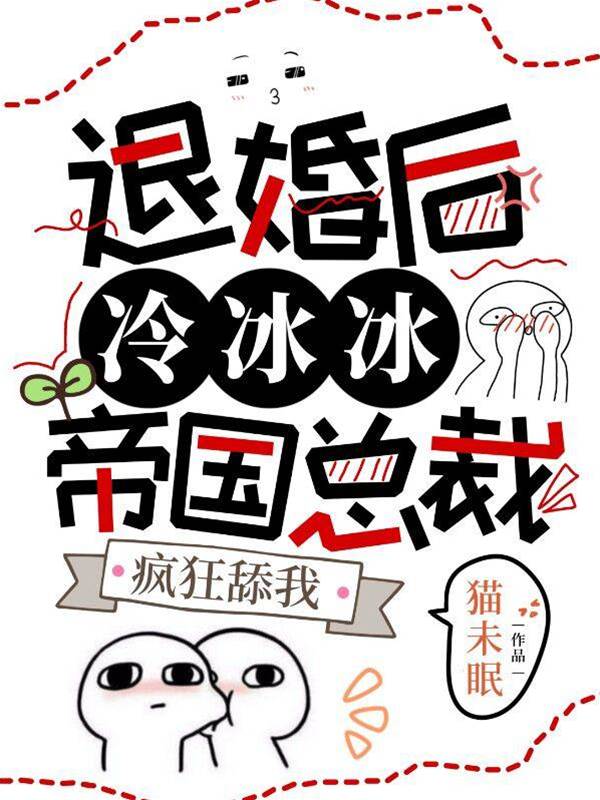《我靠裝白蓮騙過了全世界》 第215章 215.夢魘
那人自知多,沒有再說話。
但是心裡對躺在床上毫無聲息的人難免有一怨懟。
雖然組織裡的叛徒已經解決,但是多留在這個地方一分鐘就會多一分危險。
要不是這個人傷過重,強行轉移可能會讓遭遇生命危險,boss也不會幹脆直接留下來照顧,延誤自己的撤退時間。
不過是隨手撿到的一個人而已,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也不知道boss為什麼對這麼上心。
保鏢心裡腹誹,麵上卻不敢表現出什麼。
男人站直,視線輕飄飄地的掃向窗外。
窗戶相識許久沒有人打掃,明的玻璃上沾染了不灰塵和油汙,窗柩積聚了撲灰,從窗戶往外看,原本碧藍的天都像是潑灑上了星星點點的灰。
男人的位置在公寓的二樓,下麵是一條羊腸小道,空曠曠的,看不見半個人影。
「楚河還沒回來嗎?」
楚河已經出去了二十分鐘,超出了他平時離開公寓的時長。
保鏢臉上的神頓時張起來。
他有些張惶的看向窗外,但是沒有男人命令,又不敢離開屋子半步,忠實的守在房間門口。
為防止臥底死前泄報,男人已經讓組織的其他員全部撤退,隻留下他自己、醫生楚河和心腹稚影。
稚影和他都是練家子。
Advertisement
再加上常年遊走於黑暗中,氣質和常人相比不同。
兩人一出去,太容易被盯上。
採購資和藥品的重擔就落到了楚河上。
他們藏的地方樓下就有一間藥店,不遠還有一個菜市場。
楚河平時出門一般隻需要十分鐘左右就會回來。
就在稚影心中煩悶,就要向男人提出讓自己出去尋找楚河的想法時,房門傳來鎖眼轉的聲音。
稚影的心頓時提到嗓子眼裡。
修長的手指握槍支。
全進警戒狀態。
男人一直沒說話,此刻狹長的墨瞳微微瞇起,腳步輕輕上前,不著痕跡擋在了床前。
伴隨著開門聲響起的是一道弱弱的聲音:「是我……」
稚影:「……」
……
他黑著臉把人放進來。
「你怎麼鬼鬼祟祟的?」
連暗號都沒敲。
害得他還以為是其他人到他們的藏之了。
楚河抓抓頭髮,從語氣中就聽出了他的想法:「雖然不是抓到藏之,但也差不多了。」
楚河進門,稚影纔看清楚河的全貌。
男人上穿著再普通不過的黑恤和黑長,細看之下才能看出上沾著的灰。
手肘,胳膊肘上均有傷。
碎發被細汗黏在額間,整個人看上去比平時的溫和文雅狼狽了不。
「弗朗那個傻,長之前對他還不夠好嗎?他媽的把組織的訊息出去就算了,還要對長趕殺絕!」
Advertisement
楚河難得了口。
稚影不解:「弗朗?他不是已經死了嗎?」
「他沒有。」
和他一樣獨一人,從那邊死亡叢林中走出來的男人,怎麼可能這麼輕易死掉。
男人勾,嫣紅的薄揚起了一點像是笑的弧度,漆黑的瞳仁中卻生冷的沒有任何緒。
稚影恍然喃喃:「怪不得長要咱們留在這裡,原來隻是想製造我們離開的假象,因為弗朗要是沒死的話,必然會封鎖長的撤退路線……」
守在原地,最危險的地方反而是最安全的地方。
任誰都想不到,van居然會膽大到一直潛藏在敵人的腹地。
「原來是這樣我還以為boss真的隻是為了這個人才選擇冒險……」
楚河沒有稚影那麼腦子缺筋。
就算長留在原地是為了避開弗朗的封鎖。
躺在床上那個人對長絕對不是半點影響都沒有。
至這麼多天的心嗬護和治療不是假的。
「弗朗已經反應過來現在正在封鎖k區,很快就會查到這裡。」
他一手抵在房門上,抬眸看一下從他進門開始就沉默不語的男人,神真摯道:「我們得馬上離開。」
他頓了下:「不包括。」
氣氛在一瞬僵。
這還是稚影第一次看楚河這麼強。
沉默幾秒,難得沒接話。
Advertisement
van也一直沒開口。
躺在床上的人皺著眉頭,像是陷了什麼深沉的夢魘,纖長的睫不時的抖,細長的手指不安的蜷。
微微蜷曲,如果不是沒有力氣,大概會直接蜷一團,像隻貓一樣。
薄薄的瓣時不時因為疼痛而發出低聲的泣。
很小。
好像隨手就可以領起來放進懷裡。
楚河說的沒錯,一個了重傷、沒有意識、沒有行能力還與他毫無關係的人,現在他們來說就是累贅。
可是……
van緩緩垂眸,修長的手指劃過孩澤淺淡、微微發白,還有一些乾裂的瓣。
冰涼的指尖順著線一路上一直到眼角。
不輕不重的勾勒孩眼眶的形狀。
的雙眼閉著。
可van知道,這雙眼睛睜開會是怎樣的景象。
很弱小,好像一隻手輕輕一折就能輕鬆折斷。
氣息乾淨。
和黑暗世界的一切格格不。
剔明亮的茶雙瞳像是流的琥珀糖,帶著一點晶瑩的質。
隻有在殺人的那一瞬才能讓人覺到糖當中裹挾的足以致命的劇毒。
明明一直在笑,也是彎的,眼睛也是彎的,就好像麗好看的月牙。
他卻未曾到有多開心。
「長,你不會現在還想帶著吧,可是刺殺你的人!」
楚河一字一頓,終於撕開了這麼多天偽裝的平和的麵紗。
「親手用匕首,刺進你的口,差一點就捅穿了你的心臟,你不會忘了吧?」
van第一次出一點真實意味的笑。
他怎麼可能忘呢?
是他親手將從那片火海中撈出來,又是他教給了在黑暗世界的生存技巧。
他隻是沒想到,他們的重逢會是在這樣的場麵。
但他在遇見之後——
確實沒打算再放手。
……
喬予安從夢中驚醒。
大腦昏沉沉的,整個人好像還沉浸在剛剛的夢境中,沒有清醒。
猜你喜歡
-
完結724 章

總裁夫人武功蓋世
在山上被訓練十八年的林依瀾終於可以下山——下山的目的卻是結婚。不近女色的冰山霍君城突然有了個山裡來的土鱉老婆,這事成了整個世界的笑柄。霍君城為了自己的自由人生,冷言冷語:“林依瀾,快點離婚!”林依瀾捏起了小拳頭,“你說啥?大點聲?”霍君城:“……………………”多年後,林依瀾受不了天天粘著她的霍君城:“你快點和我離婚!”霍君城笑著扛起人:“夫人真愛說笑,寶寶的妹妹還沒生呢,怎麼能離婚?”
137.5萬字5 20999 -
完結392 章

傅先生的小祖宗重生了
國際談判官江芙遭人陷害而亡。醒來發現自己重生在一個剛訂婚的女大學生身上。與未婚夫初次交鋒,傅奚亭語氣冰冷帶著殺氣:“聽話,就留著,不聽話,就棄了。”再次交鋒,江芙站在首都大學禮堂里參加國際大學生辯論賽,望著臺下當裁判的傅奚亭,字正腔圓問道:…
106.4萬字8.33 51543 -
連載1042 章

纏腰
十歲那年,他靦腆地喊著一聲“薑姐”,瘦瘦小小,是聽話的小奶狗,她學著大人的樣子,親他的額頭安撫。 再見麵,他一身筆挺西裝搭配金絲眼鏡,舉手投足間如皚皚霜雪矜貴清絕,高不可攀。 撕下那副斯文敗類的偽裝,他終於在黑暗中露出了獠牙。 “這不是你教我的嗎?”他從後麵環繞住她的細腰索吻,聲音帶著蠱惑,近乎玩味地喊出那兩個字,“薑姐。” 薑玖這才明白過來,對方早就在她不知道的地方,變成了一頭偏執且腹黑的狂犬。 …
104.1萬字8 14194 -
完結12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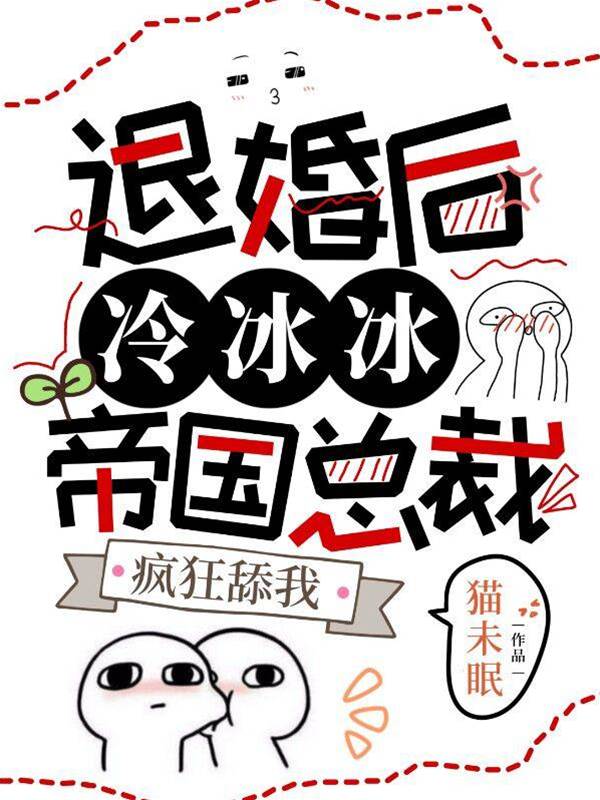
退婚後,冷冰冰帝國總裁瘋狂舔我
退婚前,霸總對我愛答不理!退婚後,某狗他就要對我死纏爛打!我叫霸總他雨露均沾,能滾多遠就滾多遠。可霸總他就是不聽!就是不聽!就非要寵我!非要把億萬家產都給我!***某狗在辦公桌前正襟危坐,伸手扶額,終於凹好了造型,淡淡道,“這麼久了,她知錯了嗎?”特助尷尬,“沒有,夫人現在已經富可敵國,比您還有錢了!”“……”
29.4萬字8 15706 -
完結158 章

深淺不一的校服時光
深淺不一的印記,塵封已久的回憶。 回到那個青春時代,回憶像各種調味劑一樣,讓我一一品嘗。
35萬字8 34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