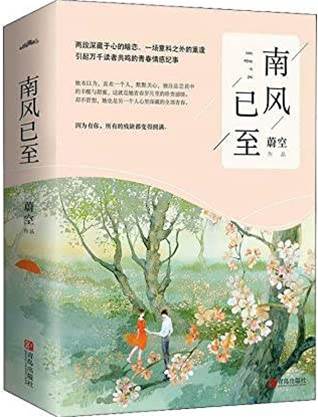《百無禁忌,她是第一百零一》 第29章:除非是死,他都不會鬆開
孫哥等人互相對視一眼,「溫老頭,你竟然還請了幫手,我們真是小看你了。」
「婿,婿你來了。」溫父直起,激的想要上前去握顧平生的手,卻在他的冰寒森冷的目中,將手重新給收回來。
「原來你就是他那個有錢的婿,欠債還錢天經地義,想必你也不缺這一百多萬,我們不想要惹事,隻要拿到錢,我們馬上就走人。」孫哥說道。
顧平生骨骼分明的手指進西裝襯的口袋,夾出一張銀行卡:「這裡麵正好有一百一十萬。」
孫哥想要去拿,但顧平生卻夾著銀行卡避開,「錢你可以拿走,昨天你們劫持我妻子的賬又該怎麼算?」
「劫持?」孫哥指著溫父溫母說道,「這你可就說錯了,人是這兩個人給我們的,就連葯也是他們自己下的,你還不知道吧……這兩個人想要拿著你妻子的艷照和視訊迫以後乖乖聽話,所以纔跟我們達了易。」
Advertisement
一推三六五,孫哥自然把責任推卸的乾淨,不過也不算是冤枉了他們。
顧平生靜默的聽著,眸漆黑一片,不見底,數秒鐘後,他將卡丟給孫哥。
孫哥這夥人隻是為了錢,現在既然拿到了錢,自然沒有留下來的必要,「我們走!」
見要債的人走了,債務也還清楚了,溫父溫母臉上也就重新出現了笑臉。
「婿,這次多虧了你,如果不是你來的及時,還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事。」在顧平生麵無表之下,溫父訕訕的說道。
顧平生坐在沙發上,手臂撐在上,狹長的眉眼抬起:「兩位,不關心一下夏夏的況?現在……人還在醫院。」
溫父溫母聞言麵一僵,笑容尷尬而勉強:「知夏怎麼住院了?」
顧平生削薄的角噙著抹寡淡涼薄的笑意:「這個問題,是我該問你們,我妻子怎麼無端的就會中藥?」
Advertisement
兩個人自然什麼都說不出來。
溫了川看了自己的父母一眼,失的垂下眼眸。
顧平生原本也沒有想要從他們的口中得到什麼解釋,他抬起手,後帶著的保鏢便已經上前,按住了溫父的手指放到桌子上。
「喜歡賭是麼?」他勾問,「哪隻手喜歡賭?」
「你們要幹什麼?!你們要幹什麼?!」溫父意識到他想要做什麼,驚恐的喊道。
溫母被溫了川攔下。
顧平生看了溫了川一眼,轉向於驚恐中的溫父,輕描淡寫道:「我的錢,可不是那麼好拿的。切掉他一手指,給他長長記。」
話落,隨著溫父的一聲慘,保鏢切麵整齊的斷了他一手指。
腥味傳來,顧平生皺了下眉頭:「把協議書拿過來,讓他們挨個簽字。」
保鏢從檔案袋中,將斷絕關係的合同拿出來。
「從今天起,溫知夏跟你們沒有任何關係,如果有人再去打擾,我不敢保證,你們還能生龍活虎的站在這裡。」他起,長玉立,慢條斯理的理了下袖口,準備要走。
Advertisement
「姐夫。」溫了川追上來,看著他的背影,大聲問道:「你不讓我們接近我姐,是為了不想要再到傷害,還是……你不想要任何人接近?」
前者是關心,是護,是珍視;後者……是錮,是偏執,也是掌控。
顧平生頓住腳步,轉。
「保護如何,掌控又如何?」他眼眸深黑:「你能如何?」
猜你喜歡
-
完結1432 章

總裁強勢愛:染指,小甜妻!
「看過,睡過,還敢跑?」堵著她在牆角,他低吼。「家有祖訓,女孩子隻能和自己的丈夫同居。」她絞著手,瞎謅。「家訓沒教你,吃完必須得負責?」「……」他是薄情冷性的軍門權少,唯獨對她偏寵無度,染指成癮。蘇晨夏,「我還是學生,娶了我,你就沒點摧殘花骨朵的罪惡感?」他鄙夷,「二十歲的花骨朵?我這是在灌溉!」
127.4萬字8 96880 -
完結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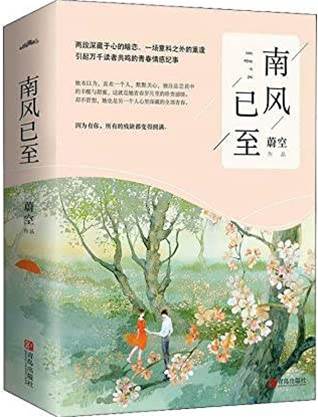
南風已至
——我終于變成了你喜歡的樣子,因為那也是我喜歡的樣子。 在暗戀多年的男神婚禮上,單身狗宋南風遇到當年計院頭牌——曾經的某學渣兼人渣,如今已成為斯坦福博士畢業的某領域專家。 宋南風私以為頭牌都能搖身一變成為青年科學家,她卻這麼多年連段暗戀都放不下,實在天理難容,遂決定放下男神,抬頭挺胸向前看。 于是,某頭牌默默站在了她前面。
22.2萬字8 6582 -
完結1748 章

錯嫁成婚:總裁的私寵新妻
被閨蜜設計,本以為人生毀了,誰料卻陰差陽錯進錯房間。一夜醒來,發現身邊躺著一個人帥腿長的男人。而且這個男人還要娶她。這就算了,本以為他是個窮光蛋,誰料婚後黑卡金卡無數隨便刷。引得白蓮花羨慕無比,被寵上天的感覺真好。
316.1萬字8.18 94776 -
完結434 章

離婚後冷她三年的陸總膝蓋跪穿了
【誤會賭氣離婚、追妻火葬場、豪門團寵、真千金微馬甲】確診胃癌晚期那天,白月光發來一份孕檢報告單。單向奔赴的三年婚姻,顧星蠻把自己活成一個笑話。民政局離婚那天,陸司野不屑冷嘲,“顧星蠻,我等著你回來求我!”兩個月後——有人看見陸司野提著一雙小白鞋緊跟在顧星蠻身後,低聲下氣的哄:“蠻蠻,身體重要,我們換平底鞋吧?”顧星蠻:滾!陸司野:我幫你把鞋換了再滾~吃瓜群眾:陸總,你臉掉了!
43.2萬字8 210740 -
完結138 章

沈總,太太說你不行去排隊離婚了
傳言,沈氏集團繼承人沈晏遲,爲人高冷,不近女色。只有江迎知道,這男人私下是個佔有慾及強的色批!*江迎暗戀沈晏遲多年,最終修得正果。結婚一年裏,沈晏遲從不對外公開。直到他所謂的白月光回國,出雙入對豪門圈子都知道沈晏遲有個愛而不得的白月光,看到新聞,都嗑着瓜子看江迎笑話,說這勾引來的婚姻,註定不會長久。…江迎漸漸清醒,...
27.8萬字8.18 280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