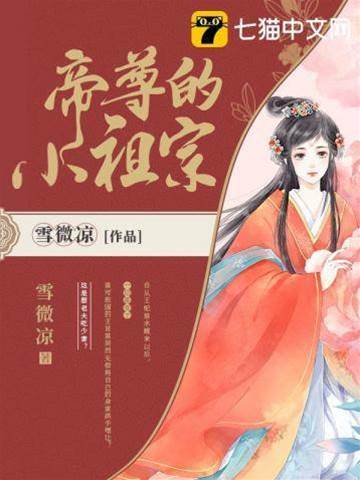《富貴不能吟》 第488章求個公平
至於許潛這麼做的原因,皇帝話裡的重點都在容家姐妹上,顯然多半是硌應著容家姐妹、甚至是容敏的份。書趣樓()
但知道自己不能再問下去了,皇帝能跟說這麼多,已經不容易。
然而,這世裡他聽到蕭珩與燕棠打架的訊息就奔過來了,且還並沒有再遮掩的說明瞭事實。
那是不是可以這樣猜想,其實原本他並沒有打算把這件事瞞一輩子,而或許是打算著等他功歸來的時候就將他世昭告天下?
隻不過前世裡出現了那麼一場誰也沒有料想到的意外,使得一切都偏離了原來的佈署?
畢竟,他剛才還在問關於如何置容慧的意見。
前世裡並沒有人給他意見,他既然又那麼想要做個信守承諾的人,可見不想讓這件事公佈於眾也很有可能。
因為事如果公佈出來,許潛從中的行為暴,那麼燕棠的死,他這個當皇帝的未必不會牽連,天下人介時私下如何揣測他,揣測到什麼地步,對天子的威信產生多大影響,彷彿可以想象。
而他顯然更不可能把這背後的人拖出來頂缸——如果能,他剛才大可以直接跟說明白那人是誰。
所以燕棠死後,將燕棠的份索瞞下來,看上去是對活著的所有人都好的一種做法。
皇帝看著長久沉默的,心裡也不那麼好。
Advertisement
從他知道徐夫人就是容慧那刻起,他約就知道有些事不可能再瞞得住。
哪怕他不說明白,以及燕棠他們總歸還是能猜得到。
他以為至會質問他幾句——總歸是他不對,害得燕棠竟差點死在自己姨母手上,又被蕭珩介懷了那麼多年,他倒是已經做好準備,把他本想要維持的那份赤誠擱置到讓暗裡鄙棄一番的地步的。
也許這些天他都並沒有覺得好過。
他一心想要做個臣子們心裡的英明帝君,可到頭來又得到了什麼呢?
於段鴻飛,他沒有照顧好他的妻兒,於容敏,他沒有找到容慧,於燕棠,他沒有做到讓他能在凱旋歸京後在榮譽之下接自己的世,於蕭珩,他甚至還讓他落下了怨恨。於那個人——他終究也談不上對得住。
「有些事,朕也是不由己。」他像往常一樣自如地坐著,淡淡吐出話語,保持著他表麵上的君威。
很多時候你的份越是重要,則越是難以任,普通人能輕易做出的抉擇,到他這裡也許會增添倍的難度。
「容慧一旦決,那麼當年的事難免會生出許多猜測。朕為皇帝,不能不以朝局的穩定為先。」
眼下的盛世太平雖然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勞,但他也不想因為自己的失誤而攪全域。
戚繚繚想起前世燕棠死後朝上的文武大。
Advertisement
盯著地板的目抬起來:「臣聽說皇上下旨任燕棠為帥之後,朝上就生出了不質疑,這次大軍凱旋,臣以為息事寧人很可能會引來更大的。
「暗殺元帥都能就此姑息,皇上就不怕將士們有卸磨殺驢的猜疑?以及於文們,會不會因此誤導他們開始胡揣測聖意?」
皇帝看過來。
戚繚繚道:「臣不敢讓皇上為難,但請給燕棠一個公道。容慧應該公佈份,也應該接決。」
畢竟是君為臣綱,若是前世那般,先不說皇帝息事寧人究竟正不正確,隻說他出發點是為朝局考慮,要下來也沒有人敢說什麼。
但是這世不一樣,不是人沒死,而且經歷過燕棠之死的事件後,便沒辦法不求公平。
再者,是沒有辦法要求皇帝對這兩世的事負責,但是最起碼,他也不應該再以維護他君王的利益優先做出選擇。
每個人做錯事都應該得到相應的懲罰,這就是王法與道德的意義。
不能讓他就這麼飾太平過去,讓燕棠的被害變得不明不白,需要讓天下人知道在這件事當中,皇帝和容慧各自都自以為是地給燕棠造就了什麼樣的命運。
「你這是在朕?」他擰起眉頭。
「不。」提起子跪了下去,「皇上對燕棠的照顧與護,就如同燕棠的另一個父親,這點任誰也不能抹滅,也永遠都不能否認。
Advertisement
「臣和戚家,誓死會陪著燕棠以滿腔熱和忠心來回報。
「可是皇上,楚王作為您的親兒子,已經因為這件事而委屈了那麼多年。您能忍心再讓您親手栽培大的燕棠開始另一場看不到終點的委屈嗎?
「皇上的仁,本就是黎民之福,讓天下百姓看到皇上對功臣的惜,您這二十年的照顧和關,不是更加有意義嗎?」
皇帝手裡的鎮紙一頭搭在桌麵上,一頭握在他手裡,半日才啪嗒一聲,落下桌麵來。
……
蕭珩的傷並不妨礙行,早上聽說戚繚繚已經出門了,他去醫房換了葯,便也順路往院子裡來。
又聽魏真說不在屋裡,隻好又先彎到燕棠屋裡來看看他。
燕棠因為傷了肋骨,隻能平躺著,餘覷見他大搖大擺走進來,也沒理會他,隻直視著帳頂的織紋。
「還有幾日就回京了,你這殘樣,能行嗎?」蕭珩在他腳榻上坐下來,兩手向後搭在床沿上,扭頭脧著他。
「你若想留下來伺候我,我留下也沒有什麼要。」燕棠喃喃說。
蕭珩哼笑,正要說話,門外忽然傳來聲音。
抬起頭來,就見戚繚繚先進來掀了簾子,然後躬立在門側,接著金燦燦的袍擺一閃,皇帝進來了。
進門後將他們倆看了一,他目落在坐沒坐相的蕭珩上。..
蕭珩站起來,燕棠也下意識地要起。
李芳上前製止,搬了椅子給皇帝坐。
「看來說幾句話是沒有問題了。」皇帝溫淡地著床上,然後抬頭跟戚繚繚和李芳道:「你們下去吧。」
戚繚繚彎,頜首與微笑的李芳出來了。
迎麵有風吹過來,掠過臉上時乾乾的,這樣的時節,真是讓人無比想念起京師來了。
(求月票)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