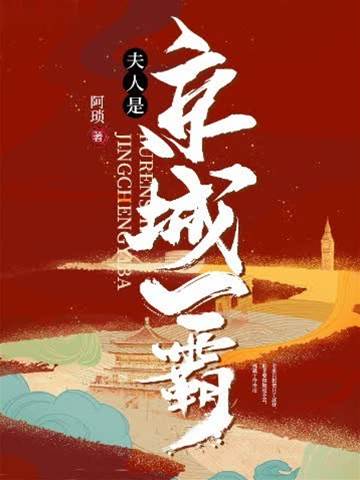《簪中錄》 第98章上窮碧落(3)
鄂王李潤往常只要無事,一直都靜待在府中,今日李舒白又已派人知照,因此他們到的時候,他已煮好了茶,靜候著他們的到來。
在他的手邊,放著一個扁平的盒子。
“四哥,聽說同昌在平康坊出事了?”他親手為他們斟茶,沸騰的茶水煙氣裊裊,氤氳的氣息讓整個茶室都變得虛幻起來。
李舒白點頭道:“是出事了。”
“傷了?”他又問。
李舒白搖頭:“已經薨逝。”
李潤頓時手一滯,有一兩點茶水濺到了外面,他卻毫無覺,只怔怔地看著在茶杯中旋轉的茶沫子,嗓音艱得仿佛是從口出來的一樣:“是……怎麼死的?”
“是被最珍的那支九鸞釵刺死的。”李舒白說。
“誰刺的?”他又追問。
李舒白搖了一下頭:“當時場面混,沒能抓到兇手。”
李潤放下茶壺,發了一會兒呆,低聲說:“同昌為公主,怎麼可能就這樣死得不明不白,簡直是匪夷所思……”
“最匪夷所思的,卻不是公主的死,而是……”李舒白示意黃梓瑕將帶過來的那幅畫放在幾案上,展開給他看,“七弟見過這幅畫嗎?”
李潤點頭道:“在張行英家中見過一次。這沒想到……當時我們幾個人指著上面的這三塊涂,隨意笑語……居然全都真了。”
“嗯,我也聽說了。”李舒白嘆道,“這幅畫,我也在同昌遇難之前曾見過,卻并沒有太過放在心上。當時要是能察覺出異樣,或許今日,也會有不同。”
“其實我……早已覺得這幅畫不對勁。”李潤面遲疑,艱難說道,“第一眼見到的時候,就覺得這事太過詭異,就算我后來回到府中,翻來覆去想了這好幾日,也依然沒有頭緒,恐怕只能請四哥為我解答疑了。”
Advertisement
他說著,取過邊的那個扁盒子,將它打開。
里面放著折疊好的一張紙,似乎是府中侍繡娘們用來描花樣用的舊棉紙,上面用眉黛潦草繪了兩三團黑墨。這幾團涂,與張家的那幅畫一樣混不堪。
李舒白和黃梓瑕對一眼,李舒白拿起畫,示意過來一起看看。
這是一張手帕大小的棉紙,繪畫的人顯然毫無功底,線條歪斜無力。可以看出的是,這兩幅畫,基本的廓是一樣的。第一幅,一團黑墨上一條細線;第二幅,橫七豎八的線條圍饒著不知所云的墨團;第三幅,連在一起的兩塊黑,一塊在上,一塊在下。
張家的畫勉強可看是三個人死亡時的模樣,這幅畫與之大致廓相同,細節卻對不上,完全不知所云,只能看是三個墨團。
李舒白看了許久,將這張畫遞給黃梓瑕,然后問李潤:“不知四弟這幅畫,從何得來?”
李潤手捧著茶杯,輕聲嘆道:“不敢有瞞四哥,這幅畫,是我母妃畫的。”
黃梓瑕與李舒白都是微微一怔,沒想到這畫居然出自李潤母妃之手。黃梓瑕不知皇家辛,李舒白卻十分清楚,李潤的母親陳修儀溫婉順,善人意,因此先皇不豫的那幾年,一直都是服侍著。
先皇駕崩那一夜,因悲傷過度而崩潰,以至于神志不清,形同癡傻。李潤在征得太妃們同意后,將母妃接出宮在自己王府供養。
“母妃去年薨逝了。在去世前幾天,仿佛回返照,認出了我。可能是上天垂憐,我本來以為,記憶中的我,會一直是十年前我時的模樣。”他角像往常一樣,含著微微的笑意,可眼中卻涌上了水汽,“母妃趁著自己最后的清醒,將這張畫給了我。那時我本不在意,但到去世之后,我才發現,這是母妃親手給我的,唯一的東西了。所以雖然覺得是我母妃發病時畫的東西,但也一直放在書房。直到前幾日,我在張行英家中,看見了這一幅畫……”
Advertisement
他的目轉向那幅先帝筆,臉上疑濃重:“可,為什麼父皇會留下這樣一張畫,而我的母妃,為什麼在犯病十來年之后,還要畫出這幅畫,并且到我的手中呢?”
黃梓瑕捧著那張棉紙,問:“請鄂王爺恕奴婢冒昧,太妃在將這幅畫給王爺時,可曾說過什麼?”
“母妃說……”他默然皺起眉,目示意左右。等所有人退下之后,他才輕聲說,“母妃那時意識不清,說,大唐天下……”
大唐天下就要亡了。
但他始終還是不能出口,只能輕聲說:“顛三倒四,可能意指天下不安,大唐要衰敗了……還說,這幅畫關系著大唐存亡,讓我一定要藏好。”
李舒白從黃梓瑕的手中接過那張紙,鄭重地到他手中,說:“多謝七弟。現在看來,這幅畫必定是你母妃憑著自己的記憶,摹下的先皇筆。”
李潤捧回這幅畫,更加詫異,問:“那幅畫,是先皇……筆?”
李舒白點頭道:“我已經去府查過宮廷存檔,在先皇起居注中標明,張行英的父親張偉益,宮替父皇探病的時間是大中十三年八月初十。”
李潤回憶當時景,說道:“那時我年紀尚,但也知道父皇因誤服丹藥,自那年五月起便圣不豫,至七月已經整日昏迷。醫束手無策,我們幾個尚在宮的皇子,想見一見父皇,卻始終被宦們攔在外面,不得而見。當時京城各大名醫紛紛應召宮,卻都無能為力……”
“而張偉益,就是父皇駕崩的那一日進宮的,最后一個名醫。”李舒白低聲說道,“我已遣人詢問過他當年進宮事宜,據他回憶,他當年是京城端瑞堂名醫,七月奉詔進宮為父皇診脈,但父皇當時已經神志不清,但在他施針之后,確曾清醒過來。但他與宮中眾人都心知這只是回返照,召他進宮為皇上治病,求的也只是讓皇上醒來片刻,以妥善安排后大事而已。”
Advertisement
黃梓瑕低聲說:“然而,這來之不易的短暫清醒,為何最終變了先皇給張偉益賜畫?”
李舒白與李潤自然也都有如此疑,當時先皇已經是彌留之際,他所應該做的,絕對不是給一個民間醫生賜畫,而應該是部署自己后的朝廷大事。
“所以這才是讓人不解的地方。而張偉益自己,其實也是一頭霧水。因為他是在先皇蘇醒之后,便趕退下來,畢竟他一介民間大夫,怎麼可以旁聽宮廷大事?”李舒白微微皺眉道,“宮中存檔,也是如此記載。先皇蘇醒,張偉益退出。未到宮門,后面有人趕上,說皇上念張大夫妙手,欽賜筆一幅。他大喜過,趕朝紫宸殿叩拜,又收了卷好的畫,一邊走一邊打開看了一眼,頓時覺得驚愕難言。”
黃梓瑕的目隨著他們的低語,落在那幅畫上。這樣一張莫名其妙的涂,居然會是十年前先皇筆,真令人意想不到。想必張偉益第一次看見這幅畫時,也是覺得難以置信吧。
而十年后,竟然會有三樁與涂一模一樣的案上演,不得不說是匪夷所思,難以捉。
辭別了鄂王李潤,他們在濃重夜中踏上了歸程。
“你先回府,還是去大理寺?”
黃梓瑕毫不猶豫說:“回府,帶點吃的去大理寺。周子秦和張行英還在那里呢。”
他也沒有反對,只說:“回來后,我在枕流榭等你。”
黃梓瑕顧不上吃飯,到廚房提了食盒,坐王府的馬車奔向大理寺。
大理寺卿崔純湛,因為公主的事,已經趕往公主府。黃梓瑕一聽到這個消息,眼前似乎就看到了他那種慣常的仿佛牙痛發作般的神。
大理寺丞范正當值,看見黃梓瑕過來,十分客氣地與見禮,臉至今還是青的:“楊公公,您說這事可怎麼辦哪,公主啊,而且還是圣上最疼的同昌公主,居然就這麼在街頭被殺了!”
黃梓瑕嘆道:“我們如今只能先等皇上的旨意再說了。”
范跺腳哀嘆,對于衙門的其他事務完全不在意了。就連黃梓瑕說要帶著食盒去找呂滴翠都不在乎,直接揮揮手讓進去了:“子秦和那個張行英也在里面,楊公公盡管進去吧。”
天已昏暗,凈室只有一個墻中點了一盞油燈,投下幽幽的。黃梓瑕站在門口時,只看見滴翠和張行英靠在一起,那一小團跳的火在他們上鍍上淡淡的華,他們一不,只是盯著那點怔怔發呆。
周子秦正蹲在門口,看見過來,興不已地跳起來:“崇古,你來了?啊……太好了太好了,還帶了吃的來,我都死了!”
他接過黃梓瑕手中的食盒,興地到里面說:“張二哥,阿荻,不管其他的了,吃飯最大,來來來,先吃點東西!”
周子秦勤快地設下碗碟,把自己覺得最好吃的兩碗菜先放到滴翠和黃梓瑕的面前,然后又給大家發筷子。
夔王府的廚娘對黃梓瑕一向很好,給送的都是最拿手的菜,可惜四個人都是食不下咽。
黃梓瑕著滴翠,盡量用溫和的語氣說道:“呂姑娘,相信子秦也和你說過了吧,再度過來,是有些許小事,請你一定要告訴我們。”
猜你喜歡
-
完結678 章

溺寵一品小狂妻
21世紀戰地醫生,一個手榴彈被炸到碧瑤大陸,竟然成了丞相府廢柴瞎小姐!說她瞎?扯!連你眼角的眼屎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說她草包?呸!天賦逆天,做個小小測試足矣亮瞎一幫狗眼!白蓮花庶妹,負心漢太子,惡毒嫡妹……得罪她的閒雜人等,通通虐得他們哭爹喊娘!手牽俊美神獸,得瑟升級修煉,隨便玩玩藥劑,還一不小心混了個特級藥劑師!我命由我不由天,觸她底線者,雖遠必誅!可是,從天而降了一隻妖孽王爺,實力兇殘極致,還像牛皮糖一樣對她死纏爛打,上下其手?不行,作為新時代女性,她怎麼能任由被人吃豆腐呢!且看她怎麼推倒美男,把這個可惡的妖孽吃到渣都不剩!
176.7萬字8 116955 -
連載7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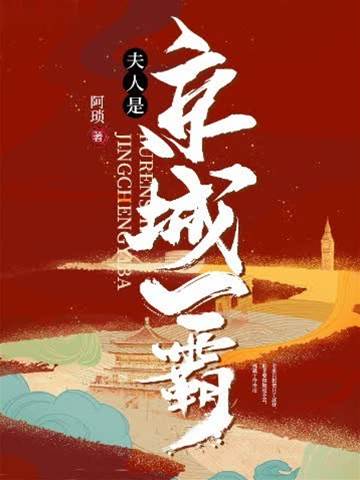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0.8萬字8 12111 -
完結554 章
穿書後,我把反派養嬌了
她來自二十一世紀,精通巫蠱毒,豈料一朝書穿,竟然變成人嫌狗厭的惡毒女配。女配娶了個入贅的醜夫,本以爲醜夫軟弱可欺,誰知人家竟是終極大反派,未來喪心病狂砍斷她四肢,將她製作成人彘。書穿後,沈青雉的目標是:洗白,瘋狂洗白!……從前他容顏絕世,卻因一場大火成了醜陋怪物。本該瘋魔狠戾滅絕人性,但有一天,他卻雙目猩紅,虔誠的跪在地上親吻她的脣……“你想要的,我都給你,我只求你不要離開我。”……你是人世唯一救贖,這顆心千瘡百孔,卻爲你柔情入骨。美強慘滅世大反派x心狠手辣大小姐,男強女強1v1。
100.6萬字8 12383 -
完結463 章

神醫貴女
他納妾當天,她摘下鳳冠給妾戴上,八萬暗衛來接,王爺和百官驚呆,想她堂堂國際特工的佼佼者,怎麼會穿越成個受氣包,叔可忍,嬸不可忍。退婚是什麼東西?好吃嗎?不過,這王爺不錯,顏好就是任性,她訕笑道:“王爺,您昨日才剛大婚,不在家陪新娘子,跑到皇宮是何道理?”
130.8萬字8 1339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