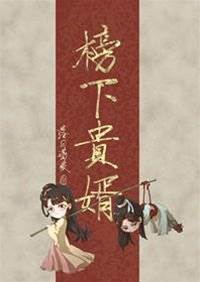《簪中錄》 第231章花萼相輝(1)
京城的流言甚囂塵上之時,天氣也逐漸寒冷,到了冬至日。
大唐在冬至日祭天,典禮繁瑣浩大。今年祭天的大禮,依然是皇帝初,皇后二,夔王三,所以李舒白一早便換好了服,前往大明宮。
黃梓瑕送走李舒白,正想著一個人在王府做什麼,周子秦已經上門來了:“崇古,今日京城各大道觀法會,可熱鬧了,來吧來吧,我們一起去看!”
黃梓瑕躊躇片刻,便換了男裝與他一起出門。周子秦還騎著那匹小瑕,那拂沙與它也悉了,兩匹馬都是溫和,互相了鼻子,十分親昵。
天氣十分冷,似乎有下雪的跡象。京中各大道觀各顯神通,在作法事的時候也是各出奇招。有的專門用漂亮俊俏的小道士念經,有的仗劍噴火差點燒著了桃木劍,還有的在演奏鑼鈸時兩個人相對飛鈸,一來一往煞是熱鬧……
他們在京中轉了一圈,路邊吃了四五次茶點,已經到了下午時分。
“崇古,你要去哪里玩?我帶你去呀……對了你現在還是末等宦?你這個月的俸祿發了麼?”
黃梓瑕無奈道:“沒有啊,現在我職業路途走得可艱難了,大家都知道我是個的,看來是不可能給我升級了,俸祿也不給我發,如今我天天在夔王府蹭飯吃呢。”
“我就說嘛,你跟著我混好了。來做我們蜀地捕頭,絕對拉風又好玩,還能現你的獨特價值,還每月給你發錢,比別人多兩倍怎麼樣?”
“不用啦,我爹娘給我留下的產業,夠我一輩子了。”嘆了一口氣,呵著自己有點寒冷的雙手,低聲說,“有夔王在,族中不敢吞并的。”
周子秦想了想,又想起一件特別嚴重的事,忙追問:“對了崇古,我問你哦,王蘊真的退婚了?”
Advertisement
“算是吧。”不愿提起此事,轉向著前方漫步目的地走去。
周子秦跟在后,郁悶地說:“王蘊這混蛋,像你這麼好的子哪里找啊?長得好看,聰明又善良,而且還能和我一起挖墳墓驗尸呢!錯過了你,天底下還能再找一個麼?”
黃梓瑕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夸自己,只能苦笑。等抬頭,看清了自己到底在何時,又呆呆地站住了。
就站在德坊之前。
十二年前,一舉名的那個地方,也是,禹宣的家。
慢慢走到當初禹宣家的門口,站在矮墻之前,看向里面。
和當年已經完全不一樣的地方,當時里面爬滿墻壁的忍冬已經不見,的石墻上全是青苔。院的石榴樹也被砍掉,青石板滿是灰塵,小渠被垃圾堰塞。院中雜七雜八地堆滿了竹籮草筐,讓乍一看還以為自己找錯了地方。
周子秦站在后,不明白為什麼站在這個院子前怔楞許久。他問:“你來這里找人嗎?”
緩緩搖頭,說:“不,我只是來看看。”
“這有什麼好看的?”周子秦轉在旁邊井欄上坐下,幫拂了拂欄桿,拿出剛買的橘子,剝了分一半,“甜的,來。”
黃梓瑕在他旁邊坐下,接過橘子吃了一瓣,才低低說道:“這里是禹宣的家。”
周子秦頓時“哦”了一聲,嘟一個驚訝的圓:“你還記得這里啊?”
點點頭:“嗯,那是我第一次幫助我爹破案。”
“如果……”周子秦著那個小院子,又轉頭看看,遲疑地問,“我是說如果啊,如果你回到十二歲,又回到這里,那個案件又在你的面前重演了……你會不會提醒你爹,讓他抓捕禹宣的哥哥,改變禹宣一生的命運呢?”
Advertisement
“會。”不假思索地說。
周子秦有點訥訥的,沒想到會回答得這麼快。
“就算我想改變禹宣的一生,也改變我家人的命運,可罪惡已經發生,我心中明知真相,又如何能為了將來的事,而刻意忽視忍耐,不去張?”著橘子,抬頭看著沉雪的天氣,緩緩說道,“但我一定會人好好關注他家的況,絕不會讓慘劇再發生。至,會好好照顧他的母親,讓不至于在喪子之后,因為悲痛而陷瘋癲,最后了斷生命。”
周子秦認真地點頭:“嗯,然后很要很要的,是好好地幫助禹宣。”
黃梓瑕仰著天空,許久許久,才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天氣太冷,的嘆息彌漫出白的淡淡霧氣,消散在翳的空中。
緩緩的,卻清晰無比地說:“不,假如能再活一遍,我不會再認識他。”
那些好的過往,那夢幻般的時,那曾經在夕下微微而笑的年——
統統都不要了。
“然而……人生并不能重來一次,不是嗎?”仿佛自言自語,又仿佛是呢喃般,深深地吸進清冷的空氣,然后將口那些堵塞住的東西一點一點出來,呼出在空中。
“走吧,沒什麼可留的了,也沒什麼可傷的。”說著,慢慢站起。
周子秦十分擔憂地看著,問:“崇古,你今后,可怎麼辦呢?”
黃梓瑕轉頭看他。
“你……和王蘊解除了婚約,禹宣又死了……”他憂慮地吃著橘子,皺著眉頭,也不知是被橘子酸的,還是心理原因,“要不,你還是來跟我混吧,你不考慮捕頭的事麼?”
黃梓瑕搖了搖頭,說:“或許以后吧,但現在,我還有事要做。”
Advertisement
“咦?什麼事啊?”他眨眨眼。
“我家人的冤案能翻案,全靠夔王。如今他邊出了那麼詭異的符咒,我得幫他將底細查個清楚。”
周子秦拍著脯說:“對啊,夔王也幫我很多,我那一套驗尸的工還是他幫我在兵部打造的呢。這事沒得說,算上我一份!”
“太好了,如果有你幫助,一定能水落石出的。”黃梓瑕點頭,說:“我懷疑,有人利用可褪的墨跡,在那張符咒上下手腳,企圖對夔王不利。”
“墨跡褪的話我知道的,我之前不是還幫你重現過那片紙灰上的字跡嗎?和那個道理差不多,我重新配一份就好了。”
“不,不一樣,這回是朱墨。”黃梓瑕皺眉道,“朱墨的配方與黑墨完全不一樣,你那個菠薐菜是無用的。而且,對方沒有在原紙張上留下任何痕跡。”
“高手啊……肯定還有我不知道的手法!”周子秦頓時雙眼閃閃發亮,興道,“我非學會不可!”
“你準備去哪兒學呢?”問。
“跟我來!”他將懷中的橘子全都丟到小瑕上的小箱籠之中,帶著就往西市跑。
到了一家裝裱行前,周子秦指著里面一個留著山羊胡子的老頭,問:“看到那個老頭兒沒?”
黃梓瑕看著這個雙手攏在大棉襖中打盹的老頭兒,點了點頭。
“他可是京城最有名的裝裱師傅,我那個菠薐菜的法子,就是在古籍上看到之后,和他一起探討出來的。”
黃梓瑕頓時肅然起敬:“你準備為了這個,專門跟他學裱畫?”
“是啊,干仵作這一行,還不得活到老學到老嗎?你忘記啦,上次夔王妃那個案件,我為了王若和錦奴手的區別,可是專門去學了骨科,還去屠宰場研究了好多豬蹄呢。”
周子秦拉著走到店去,老頭兒微微睜開眼瞄了他們一眼,有氣無力地問:“周爺,有何貴干啊?”
周子秦立即換上了諂的笑容:“易老伯,反正冬天這麼無聊,我今天又過來跟你學本事了。”
老頭兒鐵青著一張臉:“滾滾滾!老頭兒沒空陪你,上次那個菠薐菜被你吵了半年多,差點沒搞掉我老命!”
“別這樣嘛……難道你不想知道如何消掉朱墨的痕跡?”
“還用得著跟你研究?太簡單了吧,白醋可以消融朱砂啊!”老頭丟給他一個白眼。
“可是白醋有氣味啊?”周子秦一臉求賢若的模樣。
老頭驕傲地仰頭大笑:“哼哼……老頭家祖上流傳的不傳之,難道還要告訴你?”
“好吧……”周子秦說著,一臉無奈地走到柜臺前,問,“易老伯,我問你啊,你家傳的那個辦法,真的能將朱墨洗得一干二凈,不留半點痕跡嗎?”
“廢話,絕對潔如新!我易家在京城開裱畫鋪這麼多年,手上要沒有這麼點絕活,能在這里立足麼?”
“真的?”
“真的!”老頭兒梗著脖子,跟只斗似的。
“那麼……”說時遲那時快,他抓過旁邊一張裝裱好的畫,嘩的一下抖開,然后取過旁邊一碟已經半干的朱墨,干凈利落地全部潑了上去。
一直靠在椅上的易老頭頓時跳了起來,一把抓過已經被他潑得鮮紅淋漓的畫,氣得全發抖,都快哭了:“展子虔啊……展子虔的臥馬圖……”
黃梓瑕趕上一步,一看那張圖,果然是展子虔真跡,畫上的馬雖然臥在山石之下,卻有一騰然躍的氣勢,氣韻生,果然是大家手筆。只可惜如今被周子秦一碟朱砂潑上去,那匹馬就跟掛了彩似的,一鮮淋漓,實在是慘不忍睹。
“你怎麼……你怎麼抓得這麼巧?啊?”老頭兒差點沒氣瘋了,氣得吹胡子瞪眼,幾乎要把他給撕了,“旁邊那個王大學士的、劉大尚書的那些畫,你潑一百張也關系啊!你潑展子虔,你潑……我讓你潑……”
老頭兒抓起旁邊一個畫軸,劈頭蓋臉朝周子秦打去,周子秦一邊繞著店中的柱子跑,一邊抱著頭問:“你不是說可以一干二凈完全不留任何痕跡嗎?”
“我……我那法子起碼得三天!可今天人家就要來取畫了!”老頭兒一邊氣一邊歇斯底里大吼,“何況這是展子虔!要是弄的時候破了一指甲蓋,把你這混賬小子打殺一百個也抵不上!”
“好嘛……主人是誰?頂多我仗勢欺人,讓他遲三天來取畫了。”
“呸!你這個小小二世祖還想仗勢欺人?人家可是王爺!”
“……頂多我跪他家門口負荊請罪嘛。”周子秦反正一點都不要臉,毫無恥地就接話了,“對了,哪位王爺啊?”
“昭王!”
“早說嘛,昭王和我有點的,我現在就去跟他說,讓他遲兩天去取畫。”周子秦說著,抬腳要往外走時,又回頭問,“三天后就能弄好了?那我到時候來參觀。”
“滾!”老頭兒上的怒火熊熊,直接一畫軸就砍了過去。
捂著頭上的大包,周子秦灰溜溜從裝裱店跑了出來。
猜你喜歡
-
完結1227 章

太子妃她命中帶煞
冇人告訴謝橋,胎穿後勁這麼大,竟然成個病秧子。 好在親和力MAX,養的動物能打架,她種的藥草都成活。 進能製符看相、砍桃花;算命望氣,看風水。 退可琴棋書畫、雕刻、下廚、賺到銀子白花花。 竟還被太子拐回了家。 “聽聞太子妃自幼克親、命中帶煞,是個短命鬼,與太子成親,冇準都要性命不保,很快就要兩腿一蹬玩完啦!”京城秘聞。 N年後。 “皇太祖父、太祖母,今日又有人偷偷賭你們昇天了冇?!”
112.1萬字8 61695 -
完結13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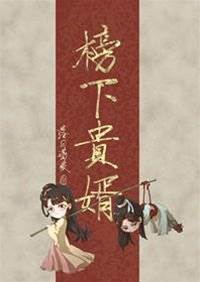
榜下貴婿
預收坑《五師妹》,簡介在本文文案下面。本文文案:江寧府簡家世代經營金飾,是小有名氣的老字號金鋪。簡老爺金銀不愁,欲以商賈之身擠入名流,于是生出替獨女簡明舒招個貴婿的心思來。簡老爺廣撒網,挑中幾位寒門士子悉心栽培、贈金送銀,只待中榜捉婿。陸徜…
46.9萬字8 7392 -
完結852 章

穿越之繼妻不好當
蘇惜竹因為地府工作人員馬虎大意帶著記憶穿越到安南侯府三小姐身上。本以為是躺贏,可惜出嫁前內有姐妹為了自身利益爭奪,外有各家貴女爭鋒,好在蘇惜竹聰明,活的很滋潤。可惜到了婚嫁的年紀卻因為各方面的算計被嫁給自己堂姐夫做繼室,從侯府嫡女到公府繼室…
229.6萬字8 2660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