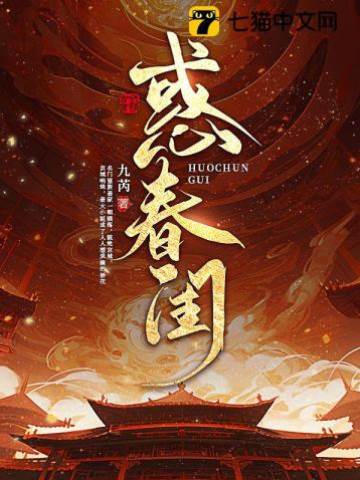《簪中錄》 第285章御香縹緲(2)
王蘊提著的心,因這一聲而頓時落了下來。他靠在廊下的柱子上,著眼前的臘梅,角浮出一笑意。
不過片刻,黃梓瑕開了門,走到他的旁。
他回頭看,見一銀紅的衫子,袖口與領口可以看出里面的緋中,深淺相配,頗為好看。他不由得注目多看了兩眼,輕聲微笑道:“我還記得,我第一次見到你的時候,你穿的也是銀紅的服。”
黃梓瑕本想說第一次見面時,自己好像是穿著小宦的服飾,過來教授王若王府禮儀。但話未出口,隨即便想到,他第一次見到自己,應該是在自己十四歲時,大明宮中。鄂王曾經說過,當年王皇后召見時,王蘊曾拉著他去看自己的未婚妻,那時的自己,確實是穿著銀紅的衫。
想到十六歲的王蘊拉著鄂王看自己的場景,黃梓瑕心頭不由得涌起一陣中混合著激的復雜緒,低聲對他說道:“是啊,難為你居然還記得我當時模樣。”
王蘊微笑著,深深凝著,輕聲說:“緋配銀紅,正如晚霞映梅花,這麼麗……我當然不會忘記。”
黃梓瑕低頭,轉開話題:“服總要配同系的好眼。”
“是啊,可不能像子秦一樣。”王蘊說著,忍不住笑了出來,“我聽說過,他娘親眼睛不好,看淺和暗都弱,所以自小便喜歡給孩子穿花花綠綠的艷服。現在長大了,其他兄弟都拒絕穿母親給選的服了,只有周子秦還樂呵呵地穿著,好像已經固定了這種穿服的習慣,即使自己穿也是那閃亮的配。”
黃梓瑕默然點頭,腦中又閃過一個無法忽視的記憶——鄂王從翔鸞閣跳下的那一夜,紫的錦之中,為何獨樹一幟穿了一件黑中單?
Advertisement
“其實,因為子秦,所以我以前還有點擔憂,在聽說未婚妻擅長查案之后,我甚至想,每天接這些的子,會不會是個兇惡可怕的母夜叉,這可不行,我一定要去看看才放心。”
聽到他的輕笑聲,黃梓瑕也跟著他在臘梅花下抿一笑。可其實,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在笑什麼。
王蘊見臉上淺淺的笑意,只覺得口氣息灼熱滌,不由走到后,自后方輕輕手將擁住,聲音溫地在耳邊說道:“那時我跟在你的后,一路走過那條開滿凌霄花的走廊,心中忐忑又張。直到你在走廊的盡頭一回頭……我看到你的第一眼,便知道我的人生圓滿了。”
他輕擁著,俯下的頭在的發上,溫熱的氣息彌漫在的發間,讓的僵,下意識地掙扎了一下。
一貫溫的王蘊,此時卻抱住了,不讓掙自己的懷抱。他側耳傾聽外面的聲響,但高墻之一片安靜,似乎沒有其他聲響傳到這邊。
他按著的肩,將近來越顯纖瘦的子扳過來,低頭凝著的神。略帶張的面容上,那眼中流出的不安與暗藏的傷,幾乎要灼傷了他。
他卻沒有如往常般放開,只抬手輕按的肩膀,俯頭在耳邊輕聲說:“如今你我雖有波折,但終究還是得眷屬……梓瑕,我此生于愿已足,定不會負你。而我,也你不要辜負我對你的心意。”
黃梓瑕聽他聲音,一如既往的溫之中,藏著微微抖的聲調,似是在恐懼,又似是在懇求一般。
覺得自己的心,也與他的語調一般,抖了起來。
一直垂在腰間的手,不由自主地,攥住自己的子。手抓得太,抖得幾近痙攣,可終究還是沒有放開自己的手,終究還是無法順理章地抱住擁自己懷的這個人。
Advertisement
閉上眼睛,任由他抱住自己。
王蘊的手上的頭發,讓將臉靠在自己的前。他面朝著庭前,隔著臘梅花看著前方的院落,依然是安安靜靜,毫無變化。
他的手握了垂下的發,在微溫的發間,一點冰涼在他的指間。是一枝銀質的簡單發簪,簪頭是碧玉雕的卷草紋,看起來,是再普通不過的一枝簪子而已。
他便沒有理會,只俯頭將面容埋在馨香的發間。他的手慢慢下去,收攏雙臂,將在自己懷中。
王蘊離開的時候,轉頭看院中,卻只見站在廊下目送他,臘梅花影幻化一片迷離的金,映在的面容上。深陷在燦爛之中,卻只浮出一蒼白的笑意,勉強送他。
他默然對點了一下頭,轉沿著走廊一路行去。
廊上的魚依舊無知無覺,在墻上鑲嵌的琉璃片之后緩緩游曳。日從后面照進來,在它們的上流轉,金紅白的鱗片閃耀著詭異又麗的線,在這條走廊中晃。
他想著藏在花影后的蒼白笑容,茫然地走過點點芒。就在走出門之時,啞仆拉了拉他的袖,口中呀呀地了兩聲。
王蘊看了他一眼,見他以手比劃著:“剛剛有人來找。”
王蘊的目轉向里面,慢慢地著,無聲問:“什麼人?”
“不認識的一位貴人,他走到小院門口,便返回了。我見他沒有進,便也沒有驚公子和黃姑娘。”
王蘊的面容上,不自覺地泛起一淡淡笑意,目卻是冰冷的。
那啞仆想了想,又示意他先別走,從屋拿出一幅裝裱好的卷軸,遞到他面前。
王蘊慢慢打開,看了一眼。卷軸是幅畫,畫上有三團類似于涂的墨團,形狀怪異,看不出什麼模樣。
Advertisement
啞仆比劃著:“是剛剛來的那位公子留下的。”
他點了一下頭,慢慢地將畫卷好,遞還給啞仆,無聲地微:“過一個時辰再給黃姑娘。告訴,是個奴仆送來的。”
啞仆連連點頭,將這幅畫收好。
“再有人來,便告訴他們,黃姑娘忙于婚事,不喜見客。”
王蘊什麼也不再說,拍拍啞仆的肩,便轉離開了。
春天將到,雖依然是春寒料峭,但地氣已經溫暖起來。
仿佛一夜之間,小庭的春草便冒出了一層,綠鋪滿了庭前。而昨日開得正好的臘梅花,卻在之下略顯衰敗,那種明的金花瓣,一夜之間似乎變得暗沉起來。臘梅那種微帶檀香的氣息,也在這樣的天氣之中顯得綿稀薄。
黃梓瑕將小幾移到庭前,在花蔭之下揮筆在紙上勾勾點點。照在的上,溫暖洋溢,偶爾有一兩朵臘梅花掉落在的上,也沒有理會,只提著筆沉思。
外面有仆人的腳步聲急促傳來,未等抬頭,周子秦的聲音已經傳來:“崇古,崇古!”
黃梓瑕將筆擱下,站起來迎接他:“子秦。”
周子秦三步并作兩步奔過來,懷里抱著個大箱子,朝點頭:“快幫我搭把手,好重啊。”
黃梓瑕幫他將那個箱子放到廊下,問:“這是什麼?”
“你猜?”他得意地把盒蓋打開。
黃梓瑕仔細一看,里面橫七豎八地躺著手腳和頭顱。頓時扶額:“什麼啊?”
“喏,你不是和王蘊快要親了嗎?這個是我送給你的賀禮。”周子秦一臉惋惜疼,“哎,真是舍不得啊!可畢竟是你要親了嘛,我怎麼能不把自己最好的東西送給你。”
黃梓瑕無奈蹲下去,拼湊著那些頭顱和軀四肢。東西手沉重,以白銅做,中間空心,關節可以連接轉,比之前著周子秦的那個銅人可方便多了。
“你看,周共刻了三百六十個道,脈絡都刻好了,還用黃銅鑲嵌出管和筋絡。”他說著,又把那個軀腹前的小銅門拉開,一個個取出里面用木頭做的五臟六腑,“怎麼樣?栩栩如生吧?我親手雕刻好又漆好的!”
黃梓瑕臉上出不忍促睹的表:“這個……我可能不需要吧,我早已悉了。”
“不是給你的,給你將來的孩子的!你想啊,將來你的寶寶一出生,就抱著這個銅人一起玩一起睡,自小就對人了如指掌,結合了我的仵作本事和你的探案能力,將來長大了還不為一代神探,名揚天下?”
黃梓瑕無語:“子秦,多謝你有心了……”
雖然,覺得小孩子還是騎竹馬、玩游戲比較好一些。
“不客氣啦,咱倆誰跟誰呢?”他有些疼地拍著口道。
黃梓瑕微笑著點了一下頭,示意下人幫把箱子搬到屋里去。周子秦坐在欄桿上,一低頭看見了幾案上的紙,便拿起來看了看。只見上面寫著:阿伽什涅、符咒、鄂王之死、張家父子之死、先皇駕崩異象、陳太妃瘋癲事。
周子秦詫異地問:“這是什麼?”
黃梓瑕淡淡說道:“是我已經查知的事。”
“什麼?這麼多你都知道真相了?”周子秦愕然將那幾個事看了又看,忍不住一把按住的肩膀,激得口水都快噴到的臉上去了,“快告訴我啊!崇古,求你了,我要知道真相!”
“不,我不能告訴你。”黃梓瑕搖搖頭,低聲道,“子秦,此案太過可怕,你知道了真相,無異于引火燒,對你有害無益。”
周子秦大吼道:“無所謂!我一定要知道!朝聞道夕死可矣!”
“不可以。”黃梓瑕抬手打開他按在自己肩上的手,認真地看著他,說道,“子秦,我無父無母,自是已經不在乎。然而你父母兄妹都在,你若出了什麼事,萬一連累到他們,你準備如何是好?”
聽到父母兄妹,周子秦頓時呆住了,許久,才結結問:“真的……真的有這麼嚴重啊?”
黃梓瑕緩緩點頭,輕聲說:“連夔王都被牽連其中,無法自保,你對自己,可有信心嗎?”
周子秦倒吸一口冷氣,只能搖頭:“還……真沒有。”
嘆了一口氣,想了想,站起到堂去拿出一個卷軸,說:“你看。”
周子秦打開一看,心裝裱的厚實黃麻紙上,赫然是三團形狀怪異的涂。他頓時愕然:“這不就是……張老伯幾次三番托我尋找的先帝筆嗎?”
猜你喜歡
-
完結153 章

重生后成了權臣掌中珠
魏鸞是公府的掌上明珠,瑰姿艷逸,嬌麗動人。她的姨母是皇后,外祖家手握重兵,自幼尊榮顯赫千嬌萬寵,在京城里眾星捧月。直到父親入獄,她被賜婚給執掌玄鏡司的盛煜。 盛煜此人姿容峻整,氣度威秀,是皇親國戚都不敢招惹的權臣,等閑定奪生死,權力大得嚇人。只是心如鐵石,狠厲手腕令人敬懼。傳聞兩人早有過節,結怨頗深。 曾暗藏妒忌的貴女紛紛看戲,就等天之驕女跌入塵埃后遭受磋磨。沒有人知道,這樁婚事其實是盛煜求來的。更不會有人知道,往后他會捧著這位名滿京城的美人,權傾朝野,登臨帝位,一路將她送上皇后之位。明珠在冠,受萬人跪拜。
52.1萬字8 38441 -
完結719 章

冒牌皇后醫天下
《冒牌皇后醫天下》有高人觀天象,蘇家應天運出天女,得之可掌控皇權穩固天下,千光國二十一年,蘇女入宮為後,帝后恩愛國之將興。 然而事實上……她是魂穿異世的巧手神醫,別人都是做丫鬟,做千金,做妃子,她倒好,直接做皇后,只是冒牌皇后不好當,各種麻煩接踵而來,所幸銀針在手天下我有,哎哎,狗皇帝你放開我! 他是手握天下的一國之帝,自古皇位不好做,危機四伏屢陷險境他理解,可為什麼自家皇后也上躥下跳的搞麼蛾子,說好的國之將興呢,說好的穩固天下呢?高人:忘了告訴您,蘇家有兩女,二姑娘才是天女! 皇上和皇后相視一笑:早就知道了。
192.5萬字8 8535 -
完結302 章

替身竟是本王自己
雙替身&追妻火葬場 全長安都知道齊王桓煊心里有個白月光,是當朝太子妃 他為了她遲遲不肯娶妻 還從邊關帶了個容貌相似的平民女子回來 誰都以為那只是個無關緊要的替身 連桓煊自己也是這麼以為 直到有一天 那女子忽然失蹤
46.5萬字8 11991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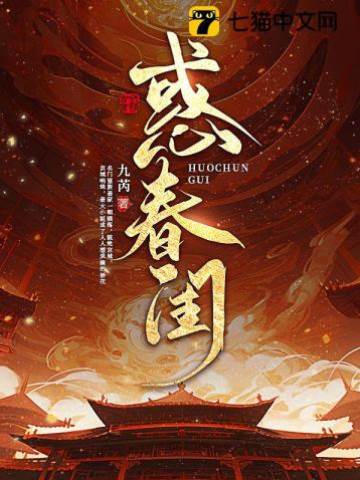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789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