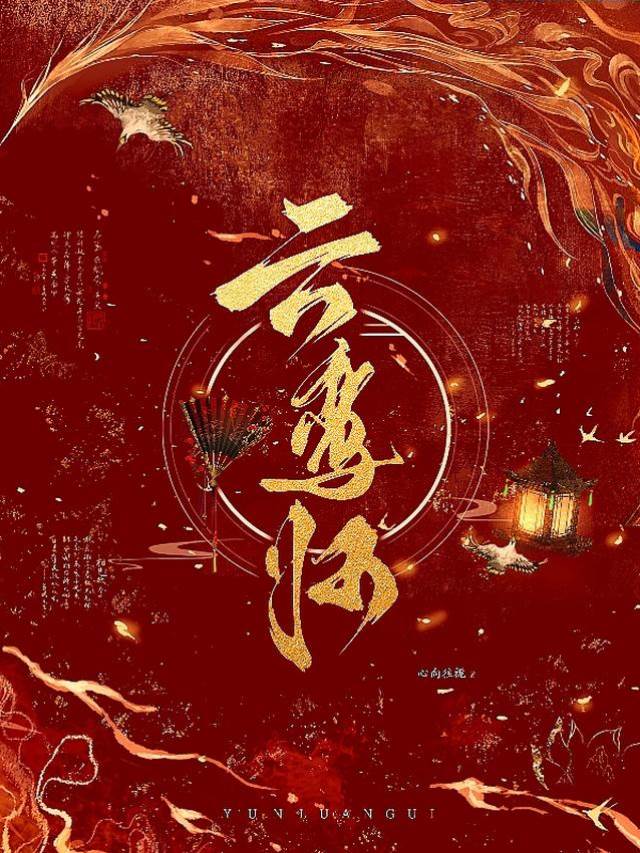《軟玉生香》 第32章 尷尬
謝青珩站在門外,瞧見陳氏衝出來,連忙朝著梁柱後一躲。
陳氏也沒留意旁邊還有人,直接捂著哭著離開。
謝青珩見陳氏出了院門之後,這才從柱子後麵走出來,過門前看了眼坐在裏麵背對著外麵一不的蘇阮。
他遲疑了下,總覺得這種況他進去有些不合適,所以轉想走,卻不想一回頭就撞上抱著手爐子,正瞪圓了眼睛看著的澄兒。
澄兒雖然什麽都沒,可眼底那神卻是明晃晃的。
你居然聽?!
饒是謝青珩臉皮厚,也忍不住差點被口水噎死自個兒,連忙低咳了聲。
“我來給……”
他想蘇阮,太冷漠,阮阮太親近,折中了下,幹脆省了名字。
“我來給送東西的。”
裏麵蘇阮聽到聲音回過頭時,就見到謝青珩那張原本冷峻寡淡的臉上滿是尷尬的模樣。
臉上剛才見過陳氏後的神還沒散去,有些冷淡的歪著頭看著他。
Advertisement
謝青珩道:“我不是有意聽的,隻是來時剛好到母親與你在話。”
他陳氏的時候倒是沒有太過別扭,拿著手上的東西示意給蘇阮。
“我來送牌位給你……”
反應過來這話不對,謝青珩又連忙改口:“我是送蘇大人的牌位過來,我已經尋了最好的匠人,照著蘇大人之前的那塊牌位造出來的,你看看覺得如何?”
蘇阮倒也沒為難他,直接示意他後,就手接過牌位將上麵蒙著的黑紗掀了開來,就見那牌位做的十分細致,約和之前在外院砸碎的那塊差不多模樣,隻是上麵還未落字。
“我想蘇大人的牌位該由你來寫,便將上麵空了下來。”
謝青珩話間從袖中取出兩墨條來遞給蘇阮:“這是他們用來寫牌位的墨條,據裏麵加了東西,寫後不易褪,我便一並給你取了來。”
Advertisement
蘇阮看了謝青珩一眼,了聲“謝謝”後,就接過了墨條,然後走到一旁將之前抄寫佛經的墨全數倒掉。
謝青珩站在一旁也沒走,而是看著蘇阮的作,見跪坐在那裏時,背脊直,然後將袖子挽起來一些,出白皙的腕子來。
的手腕特別細,上麵綁著紅繩,而拿著墨條研墨之時也與旁人不同。
先將其上刮掉了些許,將其放在指間輕撚了片刻,像是在墨條濃度,下一瞬才取了幾滴清水硯臺,將墨條放平之後直接用左手輕轉了起來。
墨平而力適中,左手反向畫著圈,竟是練無比。
謝青珩微怔,蘇阮研墨的這些作,倒是像極了那些常年書寫用筆之人,畢竟他曾經見過許多子,甚至一些不常用筆的男子,都是右手研墨。
唯有經常寫字之人,才會習慣左手研墨,右手書寫,且因已習慣,便不會覺得力道偏倚。
Advertisement
而且也隻有常年書寫的人,才會養事前“品墨”的習慣。
蘇阮沒留意謝青珩目中生出的奇怪之,隻是一邊磨著墨,一邊拿著筆想了想,等著那硯中墨濃淺合適之時,這才右手執筆蘸墨,在牌位上書寫起來。
猜你喜歡
-
完結1084 章
驚世醫妃
“說好的隻是一場交易,各取所需然後各奔東西的,請問,你這是幹什麼?” 聶韶音忍無可忍地推開眼前顏值逆天的男人。 不料,傳說中的病嬌她根本就推不動,硬生生把她給壓製在牆角:“本王所需尚未得到!” 聶韶音:“你還想要什麼?” 君陌歸:“你。” 不畏強權而死,穿越獲新生,聶韶音決定這一次:她要做那個強權! 婆家讓我做妾?休夫、踹! 娘家陷害壓榨?掀桌、撕! 王侯將相找茬?手術刀一把、銀針一盒,戰! 很好,世界終於清靜了,醫館開起、學徒收起、名滿天下! 轉身見到某人還跟著身後,她皺眉:“說吧,你想怎麼死?” 出門弱不禁風居家生龍活虎的某人挑眉:“本王想死在你懷裏!” 聶韶音吐血:“……那樣死的是我!”
190.6萬字8.21 2524413 -
完結203 章

姝色
當朝太后二嫁先帝前,曾於民間誕一女,是爲趙氏阿姝。 阿姝年不過十六,已是顏色姝麗,名揚河北的美人。 出嫁前,兄嫂皆勸,劉徇頗有城府,若以色侍君,怕不長久。 阿姝道:“都道此人溫厚儒雅,素得人心,卻從不近女色,年近而立仍孑然一身,我縱想以色侍君,怕也無從下手。” 可婚後,她方知,傳言大錯特錯! 溫厚儒雅,素得人心是真,至於不近女色—— 呵呵,半點也瞧不出來! 劉徇兄長新喪,孝期未出,便娶了仇人女, 原該水火不容,豈料不久便成夫人裙下臣, 從此一路共享榮華,登臨天下。 僞溫柔君子男主X真嬌弱美人女主
32.5萬字8 6752 -
完結28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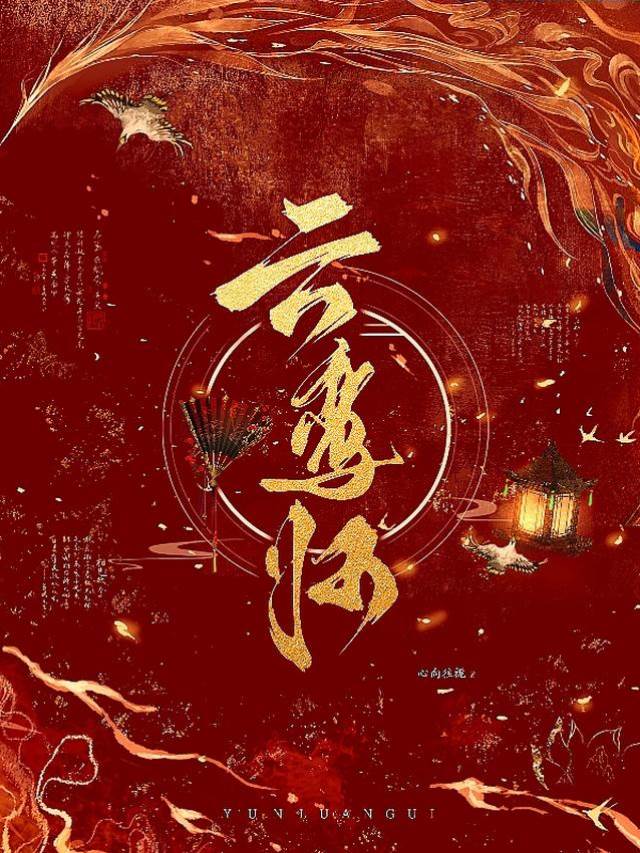
雲鸞歸
【黑蓮花美人郡主&陰鷙狠厲攝政王】[雙強+甜撩+雙潔+虐渣]知弦是南詔國三皇子身邊最鋒利的刀刃,為他除盡奪嫡路上的絆腳石,卻在他被立太子的那日,命喪黃泉。“知弦,要怪就怪你知道的太多了。”軒轅珩擦了擦匕首上的鮮血,漫不經心地冷笑著。——天公作美,她竟重生為北堯國清儀郡主薑雲曦,身份尊貴,才貌雙絕,更有父母兄長無微不至的關愛。隻是,她雖武功還在,但是外人看來卻隻是一個病弱美人,要想複仇,必須找一個位高權重的幫手。中秋盛宴,薑雲曦美眸輕抬,那位手段狠厲的攝政王殿下手握虎符,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倒是不錯的人選。不近女色,陰鷙暴戾又如何?美人計一用,他照樣上鉤了。——某夜,傳言中清心寡欲的攝政王殿下悄然闖入薑雲曦閨閣,扣著她的腰肢將人抵在床間,溫熱的呼吸鋪灑開來。“你很怕我?”“是殿下太兇了。”薑雲曦醞釀好淚水,聲音嬌得緊。“哪兒兇了,嗯?”蕭瑾熠咬牙切齒地開口。他明明對她溫柔得要死!
42.5萬字8 2182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