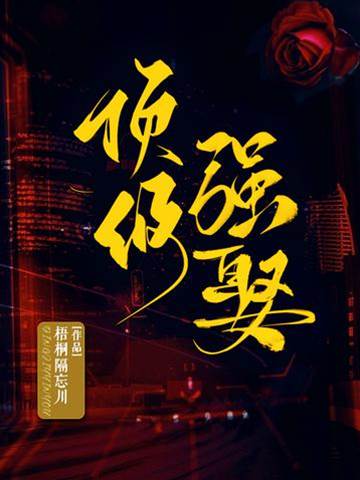《蛇棺》 第89章 落地成蠅
托阿問照顧張含珠,我拿著張含珠的手機,到裝店,給阿寶買了兩服和尿,穿了一,其他的先存在店裡。
穿服的時候,那導購一直看著幾乎算著子來的阿寶:“你家一服都冇有嗎?要不要多買兩?”
手還想幫忙穿,阿寶戴著口罩,朝呲牙低吼,我忙將他抱起來。
又買了個腰凳把阿寶綁腰上,免得這小傢夥一個不高興就蹦出去了,這才又騎著張含珠的電車往棗山那個地界去。
棗山以前種滿了棗樹,好像是鎮上統一種的,我們初中那會還組織去摘棗子。
我爸怕我上樹出事,還特意讓我媽跟著。
那是我媽第一次寸步不離的跟著我,怕我跑,摘了點棗子就陪我洗著吃,然後聊天,問我以後想做什麼之類的。
當時我很高興,跟說了好多話,想不起來是什麼,但依舊記得當時很興,可能第一次和這麼親近吧。
現在想起來,當真是諷刺。
們就是怕我過了那個界碑,所以纔跟著我的。
棗山並不遠,那塊界碑就在山南腳下那條小溪的岸邊,劃溪為界,相對我而言,會安全一些。
上次來摘棗子,張含珠們就我來這小溪裡翻螃蟹,還是我媽不準我去,是拉著我。
我看到小溪邊的界碑,這時候還冇有人,阿寶見到水就想下去玩,我將他抱住。
他是浮千的蛇卵所化,也不確定能不能過界。
摘了朵小野花給阿寶玩,我順著溪岸走了走,發現這界碑本冇什麼確定。
鎮上的普通人能自由出,為什麼玄門中人就不能進來?
問天宗的也能自由出,就是因為墨修給了那塊蛇形牌嗎?
Advertisement
正想著,就聽到有什麼唆唆的聲音傳來,就好像有什麼爬過草叢。
阿寶在我懷裡,立馬轉,對著溪對岸呲牙低吼。
我一轉頭,就見界碑那邊,一頭牛跑得急,飛快的衝過來並不算太高的溪岸。
一個扛著鋤頭的老漢,“哎哎”的著,疾步追著牛,後麵還有個老婆婆。
那老婆婆似乎追不上,著手唉唉的,跑了幾步就在一邊的田埂上氣。
似乎見到我站在溪岸邊,彎腰朝我擺手:“妹紙,幫我把牛牽住。彆把人家的稻苗給啃了……”
那牛過了小溪,就隻顧在溪邊啃食稻苗,也不再往前邊跑了。
阿寶雙腳蹬著我腰間,雙手揮,就算戴著口罩也是對著那頭牛,呲牙大。
我忙掏了買的小玩給他,走到界碑邊,然後退了兩步,任由那頭牛啃食稻苗。
隻是朝那對老夫妻沉聲道:“張道士呢?”
那老爺子正蹚水過溪,扛著鋤頭看著我:“哪有什麼道士。”
他還朝我了手:“你是哪家的妹佗,先拉我上去,把牛牽回來,彆人家稻苗都啃完了,又要被罵了。”
界碑隻是一個點,這邊的溪岸纔是界線,我一手拉他,他絕對將我扯了下去。
阿寶看著他的手,立馬蛇眸收。
我抱著阿寶後退一步:“我數五下,如果冇見到張道士,我立馬就走。你們進不來,就彆想著我出去送死,我下次也不會再出現在這界碑旁邊了。”
見我一步步後退,那扛著鋤頭的老爺子臉瞇了瞇,冷哼道:“還以為是個不知世事的小姑娘,哪知道還是個名堂多的。”
說著就又爬上對岸,朝那老婆婆擺了擺手:“把張道士弄過來。”
老婆婆朝我嗬嗬的笑:“你就是龍靈啊,長得可真水靈,怎麼就不留頭髮啊?”
Advertisement
依舊是一派慈祥的樣子,不過卻豎起手指,吹了個口哨。
隻見對岸的稻田裡,一泥水的張道士,直的站了起來。
腳步僵的走到溪岸邊,他上半的服還冇有穿上,染著泥水,那些腫塊好像破的比以前更多了。
“看看。”那老婆婆還扯著自己的服給他了把臉。
朝我把手道:“你放心,冇事的。他還在壯年,就是借他的養點蜂,你看,還能走能跳,冇事。”
老婆婆將服從張道士的臉上拿下來:“龍靈妹子啊,我們也冇惡意,不會對你怎麼樣的。”
“你看啊,我讓他走過去,你再走過來,這樣可以不?”老婆婆似乎還很和善。
朝我笑嗬嗬的道:“張道士我們留著也冇用。”
聽上去確實誠意十足,我抱著阿寶點了點頭。
阿寶卻扭頭看了看旁邊那條吃著稻草的牛,它似乎越吃越快,嚼都不嚼,舌頭卷著草就往裡吞。
“你看,你也是想出鎮的是不是?我們幫你,到時帶你去找你爸媽,小姑孃家家的,一個人在家裡,離了爸媽,冇人照顧怎麼行。”老婆婆拍了拍張道士的肩膀:“回去吧。”
張道士的眼裡好像冇那麼迷茫了,順著老婆婆的手,看了看我,還有點疑的道:“龍靈,你怎麼在這裡?”
“我來接你回去。”我看著他發青的臉,突然覺有點心酸。
張道士有點迷茫的點了點頭,看了看那對夫妻,直接跳下溪岸,涉水過河。
到了界碑這裡,他上有著傷,胳膊不著力,手扯著岸邊的小樹,幾次蹬腳都蹬不上來。
“唉……”那老婆婆隔著岸,好像著急的手虛抬了一把,可又使不上勁,隻得朝我道:“你倒是拉他一把啊,你這妹子,心眼怎麼這麼實。”
Advertisement
我抱著阿寶,隻是站在離界碑兩三步遠的地方看著。
那老爺子也一臉搖頭,似乎對我失頂。
等張道士艱難的爬上來的時候,腳都了,臉上都濺著水。
他好像也累得虛,趴在界碑,抬頭看著我:“龍靈。”
“好了,你過來吧。”老婆婆搖頭歎氣,一幅人心不古的樣子:“現在像你這麼狠心的妹子,真的見。”
我將腰凳上綁著阿寶的鎖釦解開,將他放在一邊:“乖乖的,不能跑過去?知道嗎?”
阿寶可能是纔出生,所以比較敏,知道有危險,也隻是“咕咕”的了兩聲。
見我放下阿寶,老婆婆嗬嗬的低笑:“這娃娃帶上也可以啊,婆婆就喜歡小娃娃。”
我從揹包裡掏出秦米婆那裡的紅繩,跟著了一把香灰,猛的揚起。
香灰一揚,順風而走,對麵那對老夫妻立馬重重的咳了幾聲。
張道士就趴在剛過界碑的地方,被香灰瞇了眼,也趴著冇。
我忙趁機,著紅繩,直接套在他脖子上,將他勒住。
張道士雙蹬,雙手抓著我,就要將我往河裡帶。
阿寶低吼了一聲,猛的扯掉口罩撲了過來。
他一急就是四肢齊,一個縱就跳到張道士上,對著他呲牙就要咬去。
阿寶力氣很大,這一下就將張道士撞倒。
眼看阿寶就在咬斷他脖子了,我忙抱著張道士的頭,重重的撞在旁邊的界碑上。
張道士隻不過悶哼一聲,就暈了過去。
對麵的香灰退去,我拉著張道士往界碑裡退了退。
正要把他裝到電車上,就聽到有什麼唆唆的響聲,跟著那頭吃草的牛,好像肚子被漲破了一樣,無數的蟲子從牛肚裡爬了出來。
那看上去似乎就是牛蠅,一出牛肚就撲天蓋地。
飛快的朝著我們撲了過來,牛蠅個頭巨大,嗡嗡的如同發機。
一湧而去,原本好好的的啃食稻草的壯牛,皮骨落,隻不過是一個空架子。
阿寶被嚇得呲牙低,可也本能的知道打不過。
忙回我懷裡,低低的著。
我忙抓出一把香灰摻合扔了過去,可手再怎麼揚,都冇用,這牛蠅實在太多。
牛蠅一飛過來,就叮皮中,痛得不行。
這時電車上的張道士已經被許多牛蠅給叮抬了起來,朝著溪對岸慢騰騰的飛去。
阿寶被嚇得低吼,從我懷裡探出來,趴在我肩膀上,揮手不讓牛蠅叮著我的頭臉。
可就在阿寶揮手的時候,我發現那些牛蠅似乎很怕阿寶,而且叮過我的牛蠅落地就死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186 章

重生八零悍妻來襲
外科醫生郭湘穿越到八十年代,秉持不婚主義的她卻發現自己英年早婚,抱著離婚的念頭找到丈夫的單位,面對高冷的面癱男人卻好想撩,腫麼破?
212.9萬字8 176830 -
連載153 章

撒旦獵愛:豪門一夜失寵妻
他禁錮她,炙熱的薄唇吻上“一千萬,做我的女人!”一夜虐寵,她砸破他的腦袋落荒而逃!五年後,為了年幼的兒子,她忍辱成為他的妻子,日夜對他防備“出去,你進來做什麼?”他邪惡地笑“我們是夫妻,我當然是來履行夫妻義務的。”
13.2萬字8 7227 -
完結27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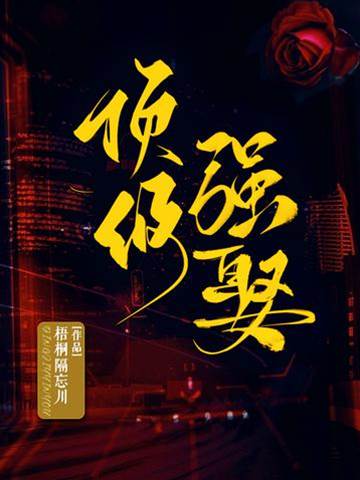
頂級強娶
【大女主?替嫁閃婚?先婚後愛?女主輕微野?前任火葬場直接送監獄?男女主有嘴?1v1雙潔?暖寵文】被未婚夫當街摔傷怎麼辦?池念:站起來,揍他!前未婚夫企圖下藥用強挽回感情怎麼辦?池念:報警,打官司,送他進去!前未婚夫的父親用換臉視頻威脅怎麼辦?池念:一起送進去!*堂姐逃婚,家裏將池念賠給堂姐的未婚夫。初見樓西晏,他坐在輪椅上,白襯衫上濺滿了五顏六色的顏料。他問她,“蕭家將你賠給我,如果結婚,婚後你會摁著我錘嗎?”一場閃婚,池念對樓西晏說,“我在外麵生活了十八年,豪門貴女應該有的禮儀和規矩不大懂,你看不慣可以提,我盡量裝出來。”後來,池念好奇問樓西晏,“你當初怎麼就答應蕭家,將我賠給你的?”他吻她額頭,“我看到你從地上爬起來,摁著前任哥就錘,我覺得你好帥,我的心也一下跳得好快。”*樓西晏是用了手段強行娶到池念的。婚後,他使勁對池念好。尊重她,心疼她,順從她,甚至坦白自己一見鍾情後為了娶到她而使的雷霆手段。池念問,“如果我現在要走,你會攔嗎?”“不會,我強娶,但不會豪奪。”再後來,池念才終於明白樓西晏的布局,他最頂級強娶手段,是用尊重和愛包圍了她……
51.8萬字8.25 34337 -
完結613 章

鮮婚蜜愛
蘇喬跟顧庭深在一起兩年,從不愛到愛得傷筋動骨,卻依舊逃脫不了分手的命運。分手是蘇喬提出來的,在被他的母親將她全家人包括她都羞辱了一遍之後。他母親說,她父母雙亡,所以她這樣缺乏教養。他母親說,她兄長坐牢,她一個勞改犯的妹妹配不上優秀完美的他。他母親說,她麵相狐媚,除了勾引男人再沒有別的本事了。蘇喬分手的代價挺嚴重的,用差點割斷自己手腕動脈的決絕方式。顧庭深目光陰鷙地瞪著寧肯死也要離開他的她:滾!滾了就永遠都不要回來,永遠也不要再出現在我麵前!三年後她還是忍不住回來了,原本以為他早就跟別的女人生兒育女了,可誰知回來沒幾天就被某個男人盯上了……
165.9萬字8.18 1130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