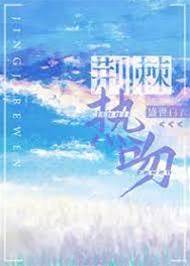《寵妻撩人:老公持證上崗》 【051】江彥丞家的老佛爺
第二天一早,不需要定鬧鐘,一到六點鐘江彥丞準時醒來。書趣樓()
去健房鍛煉了一個小時,本想去臺的沙袋上打上幾拳,又怕吵到對麵的譚璿,對於誇贊慕揚的好、鍛煉積極這件事,他小心眼地記在了心上。
被綁架的這一個月,他的狀況不好,被他老婆瞧見的瘦弱不堪,寧願去評價素未謀麵的慕揚,也不提他有多鍛煉,多健康。
從健房出來,出了很多汗,沖了個澡,廚房熬著的皮蛋瘦粥已經好了,灑了翠綠的蔥段,江彥丞用最好看的碗盛出來,放在一旁。
慕揚頂著一頭發,迷迷瞪瞪地聞到香味走進廚房,看見那粥眼睛一亮,二話不說就要去端那碗粥“阿丞,你說你平時都做什麼麪包三明治啊?我看這粥可以。”
然而慕揚還沒著碗的邊兒,就被江彥丞搶先一步端走,江彥丞手裡拿著那隻碗,用眼神示意慕揚“鍋裡還剩,自己盛。”
慕揚盯著他的兩隻手“你不是幫我盛好了嗎?你要喝兩碗啊?你有沒有那麼?”
江彥丞將兩隻碗放在餐桌上,又拿來一個托盤,將其中一碗放上去,頓了頓,回頭問慕揚“你覺得隻喝粥夠嗎?再來點什麼好?”
慕揚以為他善心大發,想了半天道“中餐你就別整麪包了,來點蛋餅啊什麼的,你會做嗎?”
“蛋餅合適?”江彥丞不確定。
慕揚笑“合適,合適,我想吃的。”
江彥丞不說話,隻點了點頭,拿手機搗鼓了一陣,看了一會兒菜譜,放下手機去開冰箱的門。
拿了兩個土豆,一個蛋,說手就手,練得像是專業大廚。
慕揚靠在廚房門前看他,賤兮兮道“我說阿丞,娶了你好,每天都有早飯吃,說讓做什麼就做什麼。”
Advertisement
江彥丞手上的作沒停,已經在平底鍋倒了油,慕揚忽然道“先別,用這個,煎出來的形狀好看。”
江彥丞轉頭一瞧,慕揚不知從哪裡翻出個心形的煎蛋。心的形狀,比他隨便放下去肯定好看,但是心形狀的餅會不會讓他老婆尷尬?
顧不了那麼多,江彥丞還是接過來,沖洗乾凈,隨後將攪拌均勻的食材倒進煎蛋。
滋滋的油炸聲裡,慕揚聞著香味,滿足極了“阿丞,你今兒個特別聽話啊!讓你乾啥就乾啥?你是不是中邪了?被人綁架回來變得這麼?”
江彥丞沒反駁,一句話直接在慕揚的七寸上“昨晚幫你服,你的後背上都是新鮮的抓痕,楚思的忌日,找人發泄好點兒了?”
聽完這句,慕揚的笑容果然僵在邊,很快又無於衷地笑起來“很正常啊,我多年沒開過葷了,找個人怎麼了?”
像是在掩飾自己的緒,慕揚故意岔開話題反問道“說真的,阿丞,你有沒有固定的人?你一個月那個幾次?總是賴在我家也不太方便辦事兒吧?”
江彥丞將蛋土豆餅盛窄盤兒中,兩麵金黃很好看,他又了一些番茄醬配,順著慕揚答道“是不方便我辦事,還是不方便你辦事?我覺得方便。”
他說著,將盤子端了出去,直接放在了托盤上。
慕揚追上去,總算看出了不對勁“唉,我說阿丞,你這放在托盤上啥意思?你要端著去臺吃?還是我們家有第三個人?我他媽怎麼覺得沒我的份兒呢?”
江彥丞點頭“最後一句說對了,來,吃飯吧。”
他還是慷慨地給將蛋土豆餅做剩的部分給慕揚推過去“吃兩塊,你吃一塊,快吃。”
Advertisement
“他??哪個ta?”慕揚看著麵前的盤子,“臥槽,ta的是心,我的是邊角料,江彥丞你缺德不缺德?”
“我連邊角料也沒有。知足吧。”江彥丞隻喝粥,喝完粥看了眼時間,八點一刻。
他去洗手間洗了手、漱了口,準備進臥室換服,進去前對坐在餐桌前的慕揚道“別托盤上的東西。”
慕揚看著江彥丞,跟見了鬼似的,他真沒,他就看看這人是不是有病,這托盤上的東西他要端給誰……帶去公司勞員工?那個ta在哪兒啊?
江彥丞很快穿戴整齊出來,西裝革履,乾乾凈凈,還特意對著鏡子照了又照,手指過臉上那個傷疤。
照完鏡子,拿起手機撥電話。
電話接通,那邊的聲音除了慵懶,還略帶驚訝“嗯?早上好?”
慕揚見鬼地發現江彥丞邊的微笑放大,略嘶啞的聲音溫極了“早上好。早餐時間,我在你家門口。早餐是放在置櫃上呢,還是你現在出來拿?”
在譚璿質疑之前,江彥丞已經解釋“今天我朋友回來了,他也要吃早餐,我想做兩人份和三人份也沒有區別,所以連你們的都一起做了。你不嫌棄的話就嘗嘗看吧。”
慕揚一口皮蛋瘦粥差點沒噎死,這順便一起做了?特意給那個ta做的吧?他慕揚隻吃了幾口邊角料,他江爺連一口餅也沒捨得吃。
譚璿猶豫了會兒,隻好道“哦,好,怎麼會嫌棄……我馬上出來。”
江彥丞放下手機,立刻就端起托盤往玄關走。
慕揚也跟著站起來,拖鞋沒穿好,差點被他一腳踢飛,他跟出去“江彥丞,你在搞什麼鬼?我倒要看看你給哪位老佛爺送飯!”
江彥丞看了下802,門還沒開,大概要收拾兩分鐘,回頭低聲警告跟上來的慕揚道“噓,待會兒閉,別說話。”
Advertisement
“你還兇我!”慕揚怒了,“江彥丞你怎麼跟個孫子似的!那人誰啊?!”
“卡”一聲,802的門開了,江彥丞上前一步,擋住了慕揚的臉,今天譚璿穿了件短袖睡,頭發比昨天要整潔一點,估計是剛剛有整理過。
江彥丞看著略有點沒睡醒的臉,笑道“又吵醒你了,今天沒暴雨,可以收拾臺了。”
譚璿看了看他,又看了看站在801門的慕揚“你朋友?”
江彥丞回頭看了眼,慕揚依靠在門上,一臉看好戲的表,眼裡的促狹隻有江彥丞看得懂。
江彥丞狠狠瞪了慕揚一眼,讓他別說話。
慕揚跟譚璿揮手“hi,我是江彥丞的朋友,沒想到我家隔壁住了個這麼漂亮的姑娘。”
譚璿微笑,禮貌地打了招呼。
收回目對江彥丞道“以後不要給我送早餐了吧,不好意思的。太麻煩你了。你再送我可吃不下了。”
江彥丞端著托盤,人還站得很直,和說話時低著頭,整個人一點沒有威脅“譚小姐,那個人每天都要吃新鮮現做的早餐,如果不給做,就不肯讓我住他家了,一頓早餐抵一天房租,我其實劃算。拜托讓我多練習一下廚藝吧,畢竟我是了你們兩個人照顧了,這是我唯一的樂趣所在。”
比昨天的理由又上升了一個層次,做早餐、送飯給,了他人生唯一的樂趣所在。
譚璿從未人如此恩惠,也從不肯白白接贈與,想了想,隻好道“這樣吧,那以後晚飯我來做,如果你回來吃飯,跟我說一聲,我多準備一份。”
江彥丞求之不得,抿努力忍著不外,卻見譚璿看了看慕揚的方向,忙道“哦,不用管他,他不回來吃晚飯。”
“我回啊!我吃晚飯!”慕揚賤兮兮地沖上來,打斷了江彥丞的話,對譚璿道“麗的姑娘,別理他,就讓他做早飯吧,他一天不做早飯就不舒服。你晚飯要是有多,賞我一口也好。”
唯恐天下不的慕揚。
都是鄰居,又是江彥丞的朋友,譚璿不好說什麼,點點頭“好。”
慕揚笑嘻嘻地出手“還沒請教姑孃的名字,我是慕揚。”
譚璿手與他握了握,點頭示意“譚璿。”
“哪兩個字?”慕揚明知故問。
譚璿一愣,看了一眼江彥丞,不愧是好朋友,連問題都差不多,正準備寫,江彥丞咳嗽了一聲,對慕揚道“璿就是玉的意思,不懂去查字典,譚就是譚老將軍的譚。”
慕揚憋笑,恍然大悟“哦,譚璿,好名字,好名字。”
江彥丞又瞪他一眼,擔心說得多了餡兒,將托盤遞給譚璿“我們都吃過了,待會兒得涼了,快進去吧。”
譚璿接過來,對兩人點點頭,轉進屋去了。
江彥丞還是探替把門關上。
一關上門,慕揚哈哈大笑,拍著大笑得腸子都要打結了,江彥丞一把捂住他的,扣住他的肩膀推進801。
s今天三更結束啦,江表示你們都笑了嗎?對老婆好有這麼可笑嗎?說你呢慕揚。
寵妻人:老公持證上崗
寵妻人:老公持證上崗
猜你喜歡
-
完結1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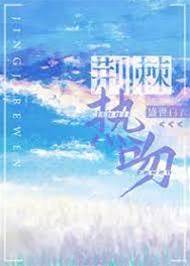
荊棘熱吻
季弦星有個秘密,她在十六歲的時候喜歡上了一個人——她小舅的朋友,一個大她八歲的男人,后來,無論她怎麼明示暗示,鐘熠只當她是小孩。她安靜的努力,等自己長大變成熟二十歲生日那天,她終于得償所愿,卻在不久聽到了他要訂婚的消息,至此她一聲不響跑到國外做交換生,從此音訊全無。再見面時,小丫頭長的越發艷麗逼人對著旁邊的男人笑的顧盼生輝。鐘熠走上前,旁若無人的笑道:“阿星,怎麼見到我都不知道叫人了。”季弦星看了他兩秒后说道,“鐘先生。”鐘熠心口一滯,當他看到旁邊那個眉眼有些熟悉的小孩時,更是不可置信,“誰的?”季弦星眼眨都沒眨,“反正不是你的。”向來沉穩內斂的鐘熠眼圈微紅,聲音啞的不像話,“我家阿星真是越來越會騙人了。” 鐘熠身邊總帶個小女孩,又乖又漂亮,后來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那姑娘離開了,鐘熠面上似乎沒什麼,事業蒸蒸日上,股票市值翻了好幾倍只不過人越發的低沉,害的哥幾個都不敢叫他出來玩,幾年以后,小姑娘又回來了,朋友們竟不約而同的松了口氣,再次見他出來,鐘熠眼底是不易察覺的春風得意,“沒空,要回家哄小孩睡覺。”
51.8萬字8.18 229746 -
完結283 章

離婚後,被他寵成全球最甜小祖宗
重生后离婚的第二天,她就被川城大佬顾辞盯上,直接成了坐拥千亿家产的顾太太。令人闻风丧胆的顾少不但长得帅体力好,而且人傻钱多,就连顾家祖产都被他双手奉上送给她!大佬对她的宠溺影响整个h国经济,顾太太喜欢什么,顾少就投资什么!她程鹿!成了整个h国行走的吸金皇后。她手撕渣男绿茶,他只心疼她手疼。她一步登天成了赫赫有名的医家圣女,他只担心自家老婆没有假期。顾少甜宠无度,可渐渐地她察觉到这男人不对劲……他为什么对她的每件事都了如指掌?每次她想要问个清楚,都被他吻到喘不过气来。程鹿:坐好了我有话问你!顾辞:这不是还没做好?老婆,咱们该添个娃了吧?
47.9萬字8 64427 -
連載426 章

至尊神醫蘇冷夏淺淺
師父說:煉藥分三種。其一,救死扶傷,治病救人。其二,匡扶正義,救治天下。其三,救己!可是,何為救己?
42.8萬字8 3422 -
完結592 章

霍總,夫人的十個哥哥又來催離婚了
趙西西意外嫁給豪門繼承人,查出懷孕的當天收到他一紙離婚協議。假千金霸占婚房,婆婆嫌棄她沒權沒勢。可從天而降六個帥氣多金的帥哥,一個是房地產大鱷,非要送她上百套獨棟大別墅。一個是人工智能科學家,送她限量版無人駕駛豪車。一個是鬼手外科醫生,每天在家給她做飯。一個是天才鋼琴家,每天給她彈鋼琴曲。一個是金牌律師,主動替她掃平所有的黑粉。一個是知名影帝,公開官宣她才是摯愛。假千金炫耀“這些都是我的哥哥。”六個哥哥集體反對“錯了,西西才是真正豪門千金。”她帶娃獨自美麗,享受六個帥哥的無邊寵愛,某個男人卻急紅了眼“西西,我們復婚好不好?”她紅唇微勾“你得問問我六個哥哥同不同意?”從天而降四個美男“不對,應該是十個!”
110.3萬字8 72679 -
完結897 章

蝕骨囚婚
追逐段寒成多年,方元霜飛蛾撲火,最後粉身碎骨。不僅落了個善妒殺人的罪名,還失去了眾星捧月的身份。遠去三年,她受盡苦楚,失去了仰望他的資格。-可當她與他人訂婚,即將步入婚姻殿堂,段寒成卻幡然醒悟。他動用手段,強行用戒指套牢她的半生,占據了丈夫的身份。他畫地為牢,他與她都是這場婚姻的囚徒。
119萬字8.18 1488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