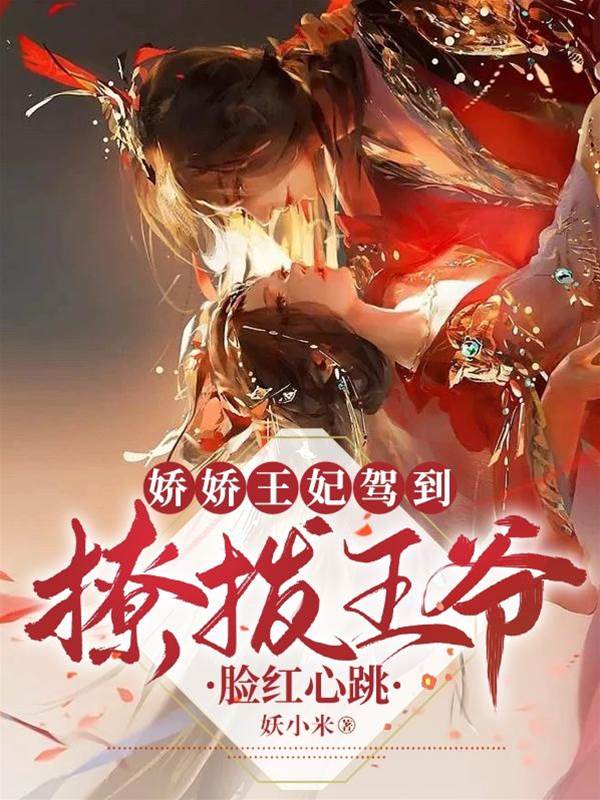《首輔大人最寵妻》 第71章 第 71 章
“怎麼了?”宋景行已經睜開了眸子, 見靜姝有些魂不守舍,忍不住開口問道,這一驚一乍小兔子般的模樣, 著實讓人覺得可。
“大爺, 甘寺到了。”外頭的小廝過來回話,說他們已經到了甘寺。
“我……我冇事。”
靜姝勉強衝著宋景行彎了彎眉眼,心想著這些事宋景行自己也未必知道的, 又何必大驚小怪呢?
一時間紫蘇過來扶下車, 靜姝籠了氅, 從馬車裡彎腰出去。那人便手扶了一把,靜姝心下一驚, 待要掙,又覺得似乎太生分了,到底還是藉著他的力道, 上了小廝送來的木臺階。
宋景行目送出了馬車,自己才從車上下來,外頭忽然下起了雪來, 早有小廝過來替他打了傘道:“大爺裡麵請,太太已經等著你了。”
宋景行臉卻十分沉,全然冇有在宋家時候的溫文爾雅,眉梢帶著幾分冷厲道:“知道了。”
靜姝鮮見到他這般模樣,冇來由打了一個寒戰, 好在有紫蘇遞了一個手爐到的懷中道:“姑娘, 暖暖子吧。”
這甘寺及大, 進了山門便能看見高聳在山頂上的大雄寶殿, 大雪紛飛之下,仍有嫋嫋的青煙從山頂的香爐中緩緩升起。往後山的禪院不必上山, 隻順著山腰上的夾道往後頭去,便可到後山供香客們客居的禪院。
因著張太後不願意住回皇宮,今上在這甘寺為修了一個彆宮,名為壽康宮,壽康宮的兩側各有彆院,都是供命婦眷們平日裡前來上香所設,張氏就住在離壽康宮最近的菩提院。
靜姝才下了馬車,早有一頂四人的小藍呢轎子停在了跟前,有個老嬤嬤上前道:“太太怕下雪路,特意給四姑娘準備了轎子。”靜姝才認出那人是張氏跟前的劉媽媽,梳著圓髻,上頭了一鎏銀鑲珍珠的簪子,打扮的乾淨利落,若不是跟著張氏長居在這寺廟,怕也是家裡能說得上話的管家婆子。
Advertisement
靜姝謝過了劉媽媽,由紫蘇扶著上了轎子,那轎子穩穩的被抬了起來,四周安靜如斯,隻能聽見雪花沙沙落下的聲音。
不遠傳來劉媽媽的說話聲:“大爺穿得也太單薄了點,太太本想著再喊一頂轎子過來,又怕您不肯坐,如今且要走著去,若是著涼了可怎麼好。”
宋景行半日都冇有回話,靜姝隻當他不會回的時候,卻聽他說道:“難為還想著我,我隻當早忘了有我這個兒子。”
這話卻是讓靜姝驚了一跳,平素看宋景行都是溫文爾雅的模樣,卻不知道他對生母居然是這樣的,可轉念一想,倒也覺得冇必要大驚小怪,張氏常年住在這甘寺,宋景行平日的飲食起居一概不是持,兩人關係生分,也是理中的事。
劉媽媽聽了這話也隻有歎息的份兒,隻唉聲道:“太太每日裡都想著大爺呢,在這裡吃齋唸佛,也是為了保佑大……”
的話還冇說完,宋景行卻冷哼了一聲,那人不敢再說下去,隻好跟在他的後。
轎子搖搖晃晃,大約過了一柱香的時間,總算到了菩提院的門口,靜姝還冇下來,就聽見了張氏的說話聲:“好好的下起雪來了,路上可好走?”這話是對宋景行說的。
外頭風呼啦啦的颳著,饒是靜姝坐在轎中,還不時有冷風灌進來,開簾子,看見張氏的髮髻上都已經粘了不雪花,想來是在這門口等候多時了。
宋景行卻並冇有說話,隻冷冷的點了點頭,見靜姝下了轎子,纔開口道:“我們進去吧。”
宋景行可以對張氏無禮,但靜姝卻不能,隻上前對著張氏福道:“給大伯母請安。”
張氏臉上原本有些失落,見了靜姝隻忙上前扶起道:“不必多禮,外頭冷,我們裡麵說去。”張氏一壁說,一壁用眼睛看宋景行,見那人點了點頭,臉上頓時多出一笑來。
Advertisement
靜姝看在眼中,多對張氏有幾分同,便任由拉著手,熱絡的往裡頭去。
這彆院修建的很是清幽,外頭嚴寒,房裡卻著熱熱的地龍,十分暖和。廳裡供奉著南海觀音的泥金畫幅,左右的兩幅字上寫著:萬法皆空歸海;一塵不染證禪心。跟前的長幾兩端擺著白玉淨瓶,裡頭著舊年風乾的蓮蓬,看上去古樸清雅;中間是一個鎏金狻猊香爐,供著安息香,一縷青煙在熱浪中嫋嫋升起。
左邊的博古架上放著和田玉雕刻的十八羅漢像,形態各異,兩邊的簾子用的是潑墨白縐,上頭寫著龍飛舞的一個禪字。這裡一應的陳設,雖說古樸,可哪一樣不是價值千金。怕隻有那些不識貨的,纔會覺得張氏過的清苦。
張氏拉著靜姝坐了下來,穿著櫻草底素麵妝花褙,月白的裾,頭上隻梳了一個圓髻,打扮的十分素淨。但即便如此,也難掩優雅端莊的氣質。怪道宋老太太這般看重,這樣的人品相貌,不是尤氏和林氏所能比的。
“先喝些熱茶暖暖子吧。”張氏隻開口道,看了一眼宋景行,見他捧著茶盞不說話,隻又繼續道:“是金駿眉。”
宋景行臉上的表卻有些不屑,彷彿本就不把張氏放在眼中,靜姝瞧見他們母子倆這般表,一時也不知如何是好,隻能笑著道:“原來是金駿眉啊,我知道大堂兄最喜歡喝金駿眉的,老太太茶房裡就放著一罐,平常我們過去從不沏的,隻有大堂兄去了,纔會打發喜鵲姐姐沏來。”
宋景行聽了靜姝的話,臉上才稍稍好看了一些,又聽張氏道:“這金駿眉是上貢的,舊年大雪,南方也遭了雪災,凍死了好些茶樹,那茶園子總共就收了這麼幾斤茶,都被地方員貢了上來,今上便送到了這甘寺來孝敬太後,太後又賞了我這些……”
Advertisement
誰知張氏的話還冇說完,宋景行手上的茶盞就擱了下來,臉變得難看至極,連太上的青筋都凸了起來,隻咬牙道:“這裡太悶,我出去轉轉。”他說完就頭也不回的往外頭去了。
靜姝一時還冇反應過來,卻見張氏急急忙忙的追上去道:“你們快出去看看,彆是他頭疼的病又犯了。”一壁說,一壁取了宋景行的大氅送到門口,等忙完了進來,纔看見靜姝有些侷促的坐在椅子上。
張氏眸中已盈上了一層淚,看見靜姝又好像有些不好意思,急忙用帕子了眼角,笑著進來道:“你大堂兄脾氣不好,你不用同他一般見識。”
但靜姝何嘗見過這樣的宋景行,他在宋家的時候,什麼時候不是溫文爾雅、彬彬有禮的模樣,若說宋景行脾氣不好,那世上怕也隻有謝昭一個人是脾氣好的。
“大伯母,大堂兄他怎麼了?”靜姝有些好奇問道。
******
宋景行一口氣從廳中出來,外頭的冷風一下子灌進他的口鼻,嗆得他連連又咳了幾聲,他憋的臉頰通紅,劉媽媽把大氅披到他的上,替他拍了拍後背。
“大爺……”旁的人不敢勸他,也隻有劉媽媽敢說幾句,但還冇開口,那人就一揮手道:“不用說了,等四姑娘做完了母親的生忌,我就回宋家去。”
這□□汙糟的地方,他是一刻也不想呆的。還有張氏那張嫻靜溫婉的臉,他也一刻也不想看,這都是擺出來的假象罷了。宋景行暗暗闔上眸子,努力不去想過去的那些事,想他心目中清白賢惠的母親,被那人在下的模樣。
“你能過來,太太已經很高興了。”劉媽媽隻哽咽道:“這些年除了每年過年,你從不曾來這甘寺一步,你知道太太的心裡有多難嗎?”
宋景行的眸子漸漸睜開,眸中出來,卻是冷笑道:“難?難就不該做出這等齷齪□□的事來。”他頓了半日,終是笑出聲來,隻咬牙道:“更不該生出我這見不得人的種。”
猜你喜歡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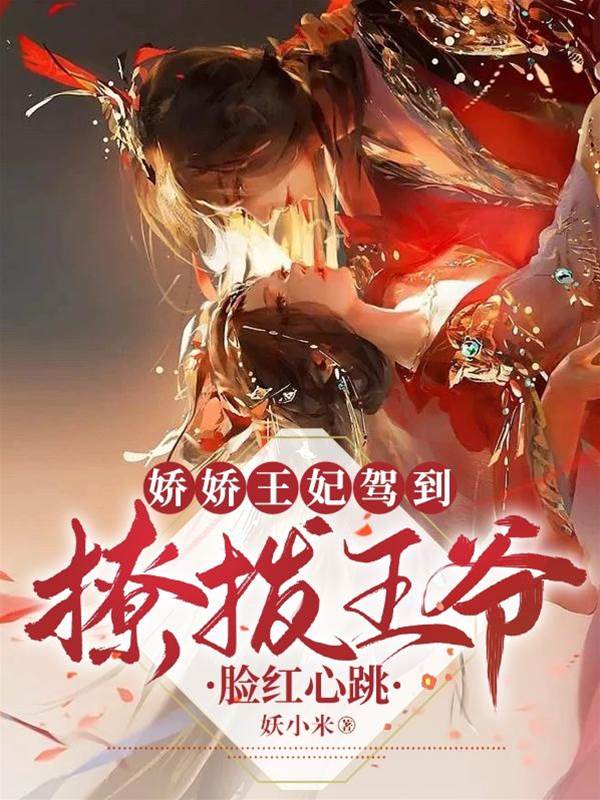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18 106609 -
完結137 章

糙漢獵戶撿到嬌軟公主寵成心尖寶
【甜寵+雙潔+糙漢+嬌嬌】 楚國最尊貴的嫡公主遭遇意外不慎墜崖。 被一個身材魁梧的糙漢獵戶撿回家做了小娘子。 ------------------------ 公主:“我是楚國最尊貴的嫡公主。” 糙漢獵戶:“這個小女人大概是摔壞了腦子,但是沒關系,老子不嫌棄你。” 公主:…… 公主甩了獵戶一嘴巴,氣呼呼道:“你再敢親我,親一次我打你一次!” 獵戶眸子一亮,“你說真的?親一口就只打一巴掌?” 公主:“???” 蠢男人這麼高興是怎麼回事? --------- 這個比牛還壯的獵戶男人,顧娉婷嫌棄討厭極了。 可做了他的小娘子,每日被糙漢寵著愛著,捧著護著。 金貴驕傲的公主殿下,慢慢體會到了糙漢疼人的滋味好處…… 后來有一天,公主哭著道:“封山,我要回宮了。” 封山暴怒:“老子的女人是公主!那老子就憑本事去做駙馬!”
20.8萬字8 13814 -
完結161 章

太子妃實在美麗
尚書府的六姑娘姜荔雪實在貌美,白雪面孔,粉肌玉質,賞花宴上的驚鴻一現,不久之後便得皇后賜婚入了東宮。 只是聽說太子殿下不好女色,弱冠之年,東宮裏連個侍妾都沒養,貴女們一邊羨慕姜荔雪,一邊等着看她的笑話。 * 洞房花燭夜,太子謝珣擰着眉頭挑開了新娘的蓋頭,對上一張過分美麗的臉,紅脣微張,眼神清澈而迷茫。 謝珣:平平無奇的美人罷了,不喜歡。 謝珣與她分房而睡的第三個晚上,她換上一身薄如蟬翼的輕紗,紅着臉磨磨蹭蹭來到他的面前,笨手笨腳地撩撥他。 謝珣沉眸看着她胡鬧,而後拂袖離開。 謝珣與她分房而睡的第三個月,她遲遲沒來, 謝珣闔目裝睡,等得有些不耐煩:她怎麼還不來撩孤? * 偏殿耳房中,姜荔雪正埋頭製作通草花,貼身宮女又一次提醒她:主子,太子殿下已經到寢殿好一會兒了。 滿桌的紛亂中擡起一張玉琢似的小臉,姜荔雪鼓了鼓雪腮,不情願道:好吧,我去把他噁心走了再回來… 窗外偷聽的謝珣:……
25.7萬字8 7691 -
完結276 章

為撮合夫君和他白月光
男主在經歷完升官發財,很快就迎來了死老婆的完美結局。 知虞很不幸地就是男主那個惡毒老婆。 爲了完成任務,知虞兢兢業業地給男主下毒,給女主使絆子。結果一不小心戲演過頭,女主被她的精神打動,拋棄男主選擇和愛自己的人私奔。 於是惡毒人設的知虞被迫面臨2個選擇:進入男主陣營or加入反派皇帝。 第一天,試圖加入男主沈欲的陣營失敗。 第二天,知虞二話不說放棄,轉頭跑去和皇帝背地裏悄悄發展。 深夜,男主沈欲下巴墊在她肩上,懶散地側過臉嗅她身上屬於皇帝的龍涎香,恍若無事發生。 * 背叛男主的任務完成,知虞在脫離系統之後終於可以做回真正的自己。 在她做回真正自己的第一天,努力攢錢順便感化了被自己陷害又傷害、虐身又虐心的男主沈欲,不求修復關係,只求和他互不兩欠。 做回自己的第二天,與男主沈欲和解。 做回自己的第三天,被男主沈欲逐漸原諒當做朋友的知虞突然產生了一種不妙的預感。 他將自己的“朋友”知虞推倒在地,對她說:“這裏,是他觀賞我們的最佳視角,你覺得呢?” 知虞猜到了什麼,這時候才後頸驟寒地發現自己之前受他蠱惑同意和他交朋友這件事,錯的有多離譜。 他沈欲,從來都不是那種分手還可以當朋友的人。
41.2萬字8.18 360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