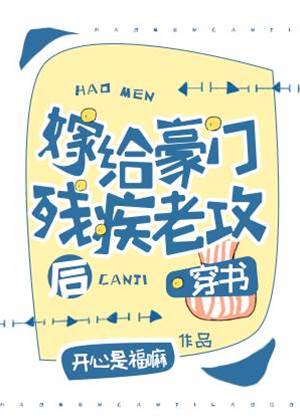《重生之深愛》 第73章
“啊?”鄭白無辜地睜著一雙眼睛,瞧瞧顧朗茳,再瞧瞧臉不太對的季斐,忽然一拍腦門,轉向旁邊開車的肖致富,“顧哥問你呢,你車上放的都是些什麼水呀,怎麼咱小哥哥喝了不對勁?”
肖致富哼了聲,繼續開他的車。
鄭白還說什麼,突然哎喲一聲慘,顧朗茳從後頭將副座放平了,鄭白猛地往後一倒,接著就被顧朗茳用手臂勒住了脖子,顧朗茳本來就算是練家子,這會兒又生著氣,手下沒留,鄭白被勒的跟只缺水的金魚似的兩眼直往上翻,“說、說,我說!放、放手,再不......放,就、沒氣了......”
季斐坐在那裡只覺得愈發難耐起來,裡像有巖漿在躥,囂著尋找出口,他熱的難,又好像不是熱,全麻麻的,像了什麼,空虛的人想死。他沒經歷過這種覺,有些慌張無措,但聽顧朗茳的話,猜測到了什麼。
他去拉顧朗茳的手,想他鬆開鄭白,可是一拉就回來了,微微了。
顧朗茳轉頭看著他,有些擔心,“怎麼了?”
季斐這時候大概也知道自己是怎麼回事了,又氣又窘,但看著鄭白鼓著的兩眼珠子,他還是冷靜地道,“你......先放開他。”
顧朗茳一鬆手鄭白就坐起來,捂著脖子猛咳,邊咳邊道,“顧朗茳你他媽的真要勒死小爺呀?我告訴你......我、我告訴我家鄭二去......”說到最後聲音就小了,他瞧著顧朗茳狠厲鶩的眼神突然有些發怵,了腦袋,忽然一扁,“就說好人不長命,我這還不是爲了幫你,哪對夫妻不是牀頭打架牀尾合,他就狠狠上他,上著上著就......更了......”鄭白的聲音又小了下去,這回不是因爲顧朗茳,而是因爲季斐,他對上季斐清冽的眼神,莫名有些心虛,乾乾笑了兩聲,“我、我這不也是爲了你們好,你要不喜歡,我、我以後不幹了。”
Advertisement
顧朗茳知道鄭白已被慣的寡廉鮮恥,就一標準的混吃混喝二世祖,加上平日都被人吹捧著,頭上又有他哥罩著,完全不知道天高地厚,你要跟他計較你就輸了。
顧朗茳直接道,“下的到底是什麼藥?”
“就、就是平常的增加......那方面想法的藥呀。”
“怎麼解?”
“這......”鄭白嘿嘿笑兩聲,有些曖昧地道,“這還能怎麼解呀,顧哥你知道的。”
顧朗茳皺了皺眉,也懶得跟鄭白糾纏了,直接對肖致富道,“去最近的酒店。”
“我、不去......”季斐的聲音微微有些啞,眼睛也有些霧朦朦的,看上去似乎有些迷茫,他咬著脣保持清醒,“你送我......回學校。”
顧朗茳握住他的手,季斐了,顧朗茳愈發握的,深深看著他,“我保證,不會做你不願的事。”
季斐看著他,終於點了點頭,看了眼顧朗茳握著他的手。顧朗茳知道這時候與他只會讓他更加難耐,連忙鬆了。季斐立即坐正,抿著脣,背脊的筆直。不知道爲什麼,顧朗茳看他這個樣子突然有種說不出的心疼。他往前去,那邊鄭白還忍不住看熱鬧,一上顧朗茳的眼神,立即掉轉了頭,心想:我就不信你是柳下惠!
去了最近的一家酒店,規格不是很大,生意也一般般,大廳裡冷冷清清的,只有一個服務員坐在那兒,肖致富先去辦了房卡,顧朗茳從車上拿了服給季斐,要扶著他上去,可季斐愣是不肯,對肖致富道,“給我張房卡就可以了。”
肖致富看向顧朗茳,見他點了頭,纔給了季斐。
一行人上了樓,季斐明顯走的有些艱難,呼吸都重了,手著房卡,他一進門就準備關門,顧朗茳一隻腳抵住門,回頭真誠地對鄭白道,“我也不裝什麼清高了,我今晚真是謝謝你了。”
Advertisement
鄭白瞅瞅顧朗茳抵住門的那隻腳,一臉我就知道的表,揮了揮手,“顧哥咱倆誰跟誰,不客氣。”
顧朗茳笑了笑,“你去洗澡吧,記得別關門,我讓致富送了人進去給你。”
鄭白笑瞇瞇的,“顧哥客氣了,哎,我要腰細長妖冶浪型的啊肖致富。”
季斐用力了門,可他這會兒沒什麼力氣,只能冷冷看著顧朗茳,顧朗茳卻不看他,對鄭白道,“還不走?”
鄭白笑道,“行,不打擾顧哥好事了。”邊走邊想,我就知道,男人啊,就不知道節兩個字怎麼寫!
等鄭白走了,顧朗茳一邊對肖致富道,“把他手機拿出來,房電話線撥了,找只狼狗送進去。”一邊側進門,啪地關了門。
季斐因爲他突然進來被的倒退了兩步,顧朗茳連忙手摟住他,發現他了,連忙鬆開,“你別怕,其實也沒什麼,我去給你放水,你等下泡一泡,自己手擼一下,多出來幾次就好了。”他說的臉不紅心不跳,直接進了浴室。季斐一張臉卻已紅了,薄紅的臉,霧朦朦的眼睛,他不知道,顧朗茳從他邊走過去的時候呼吸都重了。
季斐直直站在那兒,裡那種難以抑制的空虛卻越來越強,他忍不住抖了抖,手握著。
顧朗茳很快出來,一邊從壁櫃裡拿出酒店準備的浴袍,一邊對季斐道,“你可以進去了。”
季斐微微有些腳步不穩,可這回顧朗茳沒再扶他,只是在他後看著他,讓他自己走進浴室。
“啪”的一聲,浴室門關上了,季斐沒解服直接跳進浴缸裡,可是溫熱的水漫上來,他卻沒有了往日那種舒服的覺,反而覺得愈發難。他想了想,一咬牙,把子給解了,自己手去那。
Advertisement
可是反覆幾次,前面脹痛的厲害,就是出不來。
季斐的手都抖了,整個人開始覺得不清醒。
顧朗茳在門外守了會兒,開始沒什麼聲音,等過了一會兒,突然聽到嘩嘩的水聲,他起先沒什麼反應,驀地想到了什麼,臉沉了沉,一把就把門推開了。
進去就愣了,季斐的子已經了,半長的襯衫被打溼了,下襬著他的,出白皙細長的,他紅著一張臉站在浴頭下,眼神有些茫然。
顧朗茳只覺得頭一,勉強下了旖旎的念頭,向前走了幾步。
季斐這才反應過來,“你來幹什麼?”
顧朗茳一手,浴頭的水淋到他手上,冰冷的,他臉一變,一把關了浴頭,“誰讓你淋冷水的?”
季斐臉有些難堪,眼中閃過一窘迫,卻都掩在薄紅的臉下,他道,“我不淋了,你先出去。”
顧朗茳皺著眉頭看著他,“不是讓你自己弄出來嗎?”
季斐腦中有什麼轟然炸開,他本來就熱,這下更有一種無地自容的覺,著聲音道,“不要你管。”
顧朗茳沒說話,看他一眼,“自己弄不出來?”
季斐一下子擡眼瞪著他,可那眼神在藥力的作用下卻顯得風無比。
顧朗茳嘆了口氣,反手關上了浴室門,抱著季斐坐到浴缸邊上,浴缸邊有些冷,與的熱形鮮明的對比,季斐抖了抖,有些使不上勁地推顧朗茳,“你......幹什麼?”
顧朗茳也不多說,直接手就去□□他那,季斐一時說不出的難堪,偏偏又沒有力氣,只能乾乾坐那兒任他擺弄,一時眼睛都紅了,抿著脣,握手。
顧朗茳看他一眼,“覺得我在玩你?”他沒等季斐回答,忽然低下了頭,去含他那。
季斐整個人震了震,“你別......”尾音突然了,那已被含一個溫暖的所在,季斐猛地睜大眼,一瞬間說不出話來,神與都於一種極致與震憾中。
季斐起先還想盡力保持清醒推開顧朗茳,可是顧朗茳幫他用的一瞬間他就懵了,他本就是保守的人,平時自己打飛機都幾乎沒有,哪經過這種陣仗,尤其是他下意識裡覺得,用有些侮辱人。
顧朗茳這輩子算是一清心寡慾五好年,可上輩子卻是個中高手,那些花樣實在是信手拈來,季斐本不是他對手,很快就丟盔棄甲,完全不知何。
反覆出來了幾次,藥力總算去的差不多了,季斐整個人彷彿虛了,最後掀了掀眼皮,想說什麼,卻只喊出了個名字,“顧朗茳......”
顧朗茳拿巾幫他乾了,又拿了條大浴巾將他包起來,輕聲道,“你累了,先睡吧,我們......明天再談。”
季斐大概也是累狠了,真的就閉了眼睛睡了。
顧朗茳看著他,有一種十分捨不得的覺,他想著也許到了明天,就再也沒有明天了,心裡突然一陣刺痛。
這一晚兩個人都有些累,顧朗茳開始還不睡,將季斐抱到牀上,蓋好了被子,自己坐牀頭看著他。可是到了下半夜,終於也忍不住沉沉睡了過去。
夏天天亮的早,有些刺眼,顧朗茳聽到敲門聲,他皺了皺眉頭,起來準備開門,卻在下牀的一瞬間僵在那裡。
他站立了半晌,纔有勇氣再回過頭去——牀上空空如也。
他的季斐,終於還是走了。
他突然想起季斐對他說過的話,他說顧朗茳,我要是走了,就絕不再回來。
他的心猛然一震,拉開門,瘋一般衝了出去,門外肖致富一驚,“顧哥!”
那啥,立刻馬上就合好了!
本想一次解決,但太困了
最後那啥,大家發現作者的更新規律沒?無恥的沒有規律!!!
猜你喜歡
-
完結4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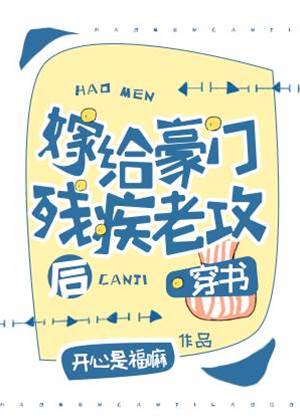
嫁給豪門殘疾老攻后
景淮睡前看了一本脆皮鴨文學。 主角受出生在一個又窮又古板的中醫世家,為了振興家業,被迫和青梅竹馬的男友分手,被家族送去和季家聯姻了。 然后攻受開始各種虐心虐身、誤會吃醋,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會變成船戲之路。 而聯姻的那位季家掌門,就是他們路上最大的絆腳石。 季靖延作為季家掌門人,有錢,有顏,有地位,呼風喚雨,無所不能,可惜雙腿殘疾。 完美戳中景淮所有萌點。 最慘的是自稱是潔黨的作者給他的設定還是個直男,和受其實啥都沒發生。 他的存在完全是為了引發攻受之間的各種誤會、吃醋、為原著攻和原著受的各種船戲服務,最后還被華麗歸來的攻和受聯手搞得身敗名裂、橫死街頭。 是個下場凄涼的炮灰。 - 原著攻:雖然我結婚,我出軌,我折磨你虐你,但我對你是真愛啊! 原著受:雖然你結婚,你出軌,你折磨我虐我,但我還是原諒你啊! 景淮:??? 可去你倆mua的吧!!! 等看到原著攻拋棄了同妻,原著受拋棄了炮灰直男丈夫,兩人為真愛私奔的時候,景淮氣到吐血三升。 棄文。 然后在評論區真情實感地留了千字diss長評。 第二天他醒來后,他變成主角受了。 景淮:“……” 結婚當天,景淮見到季靖延第一眼。 高冷總裁腿上蓋著薄毯子,西裝革履坐在豪車里,面若冷月,眸如清輝,氣質孤冷,漫不經心地看了他一眼。 景淮:……我要讓他感受世界的愛。
16.2萬字5 6117 -
完結213 章

霍總每天都不想離婚
三年前,霍圳和秦珩做了一筆交易,用自己的婚姻換取了秦氏集團百分之十的股份,以及霍家掌權者的身份,三年后,霍圳不僅在霍家站穩了腳跟,連秦氏也被他一點點蠶食吞并。 某一天,秦珩把離婚協議書擺在霍圳面前,“簽了吧。” 霍圳:“我不想離婚!” 秦珩:“不,你想。”因為再過不久,霍圳的白月光就要回國了。
82.4萬字8 1056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