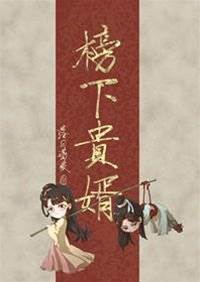《重生后王妃咸魚了》 第26章 第26章
曲風將話遞到后院,眾婢子心頭慌。
“完了,王爺定是問責來了。”
留荷擔憂不已。
雋娘先一步按住留荷的手腕,眉目爽利與沈妝兒道,
“王妃,奴婢隨您去見王爺,昨日之事皆出自奴婢之手,與王妃您無關,王爺若罰,罰奴婢便好。”
沈妝兒漫不經心換了一杏的衫,腰間系上一條同腰帶,聽雨替挽好一隨云髻,獨獨上一支點翠流蘇步搖,邁下室的臺階來到雋娘跟前,
“抗旨是我的意思,此事與你無關。”
雋娘跪在腳前不肯,將淚一拭,“王妃,您帶奴婢去吧,您是神仙一樣的人,豈能與那小宮們斗,奴婢跟著您去,王爺問起,奴婢也好一五一十說出個緣由來。”
沈妝兒想想也有道理,昨日之事確實一無所知,朱謙必定要問清經過,讓雋娘說明白也沒錯,便獨獨帶著雋娘前往書房。
彼時朱謙立在廊下,正與溫寧定好赴宴的賀禮,遠遠的瞧見沈妝兒帶著面生的子院門。
朱謙臉倏忽繃沉,上回放過了,未吃教訓,是以今日又來膈應他?
天將暗未暗,天際還殘留著一霞云,廊廡燈芒被暗青的天映得昏暗,沈妝兒一襲杏的衫自暈黃的芒里邁出,仿佛自時深走來,
眉目清,不濃不淡,干凈得如同那抹霞云,得不食人間煙火。
曲風說的沒錯,氣越來越好,配的這氣質,與以前那戰戰兢兢的小婦人不可同日而語。
沈妝兒來到他跟前福了福,“見過王爺”
Advertisement
雋娘也二話不說跪了下來,伏在地上只等朱謙發作。
朱謙看都沒看雋娘一眼,只冷眼覷著沈妝兒。
溫寧瞅了一眼伏低的雋娘,段婀娜出的線條,確實是一出眾的子,王妃當真舍得呀,也難怪朱謙近來一點好臉都沒,他已經不敢去看朱謙神,了額,輕輕走在雋娘旁,低語道,
“跟我出去”
雋娘愣了愣,抬眸看了一眼朱謙,朱謙立在柱側,暮天相接,瞧不清他的臉,大抵是不好的,溫寧是朱謙心腹,他要離開,雋娘也不敢遲疑,起再朝朱謙施了一禮,愧疚地看著沈妝兒,一步三回頭離開了。
這模樣,落在朱謙眼里,越發坐實了沈妝兒的意圖。
他扭頭大步了書房。
沈妝兒涼涼哼了一聲,跟了進去。
出門急,口有些,先往北側桌案尋了一壺茶,飲了一杯,瞥了一眼朱謙,不不愿倒了一杯給他,捧著茶盞往他走來。
朱謙立在窗欞旁的高幾旁,一雙寒眸便釘在了那枯萎的菖上。
沈妝兒順著他視線覷了一眼,暗道不好。
這是要新仇舊恨一起算。
換做前世,沈妝兒定要嚇得跪下來認罪,如今是朱謙納妾在先,豈會給好臉,便把茶盞往坐塌小案一擱,干道,
“王爺不要怪妾行事魯莽,”先把事認下來,省的牽連雋娘,“王爺堂而皇之將侍妾領門,還安置在文若閣,不是故意氣我麼?我能忍這麼久,已是涵養。”
朱謙心里的火莫名去了些,偏頭睨著,嗓音不寒而栗,“你可見我過們?人我昨夜已經置了,你倒是好,頻頻帶人往我書房來”
Advertisement
沈妝兒被前一句話給鎮住,以至于沒聽清后面一句,
“置了?怎麼置的?”
朱謙子往前傾了傾,居高臨下看著,視線所及之仿佛有刀鋒刮過,沈妝兒被得后退了幾步跌坐在了塌上,
朱謙并不打算細說,隨口應付道,“自有們的去,總之不會來膈應你。”
沈妝兒微吃一驚,抬眸他,深邃的眼,聚了墨般濃烈。
“皇后那頭呢,可有說什麼?”
朱謙俯視,那雙眼如小鹿般干凈剔,還是那般天真無邪,一個后宅小婦人而已,除了他,還能指什麼,只是想起這段時日干的事,朱謙渾又燒了起來,結來回滾,沉聲道,“事我已擺平,皇后不會尋你麻煩,王妃打算如何謝我?”
沈妝兒眸微轉,看來那二人當真是眼線,朱謙伺機將人驅逐了,如此雋娘算立了功。
于是冷聲一笑,坐直了,耷拉著坐在塌上,理了理衫道,
“王爺,既然您昨夜便置了人,為何不派個人告知我,害我擔心,再說了,此事因王爺而起,我助王爺一臂之力將人趕走,該是王爺謝我吧?”
倒也沒那麼好騙了。
朱謙負手斜睨著,語氣一松,“也對,我該謝王妃相助之力,父皇將軍監劃歸我管,如今缺一正監,我意讓你伯父沈璋調任此職,從五品升為正四品上,王妃以為如何?”
本以為沈妝兒該滿目驚喜,不想,反倒是一臉驚嚇。
沈妝兒想起前世沈家被朱謙連累,卷京城中,這一世并不想沈家與朱謙牽扯太多,轉念一想,只要是朱謙妻子一日,沈家與朱謙便被綁在一條船上,不是想回避就能回避得了的。
Advertisement
罷了,哪怕拒絕,二伯父那頭也會應下,擔任正四品監正一職,算是獨當一面,且在朱謙護佑下,不用看他人臉,二伯母也不用在寧家面前低人一頭。
緩了一口氣,慢聲問道,“真的?”
朱謙將剛剛那數變的臉收在眼底,也了打趣的心思,如實道,“我缺一心腹替我盯著軍監,你二伯父恰恰在工部任職,將他調過去最合適不過。”
沈妝兒反倒松了一口氣,若當真徇私,也就不是朱謙了。
原來是順水推舟,兩廂便宜,于是起朝朱謙施了一禮,
“那妾承王爺的”
屋一時靜默下來。
朱謙淡淡看著,這段時日因侍妾一事,夫妻二人已許久不曾親熱,面前的人兒,杏眼桃腮,如一朵開在夜里的荷,也不知在想什麼,眼珠兒咕嚕嚕在轉,仿佛轉人心窩里,他往前一步,
“請你來是與你相商,后日昌王妃壽宴,昌王邀請你我赴宴。”
原來他所謂的要事便是這個?
悉的氣息近,沈妝兒心神微頓,避開他灼然的目,甕聲甕氣點頭,“好”
猛地想起前世有一回昌王設宴,六王與昌王起了沖突,連累朱謙了傷回來,莫非是這回?
的心登時便凝了起來,下意識拽住了朱謙的袖子,“王爺,后日赴宴,咱們可以不去嗎?”
不希朱謙過多牽扯六王與昌王爭斗,那一場禍及京城的終究是心中憂。
墻角銅釭高照,芒落在眉眼,如暈開了一團絨,眼的,盛滿了擔憂,他已許久不曾在眼底瞧見這樣的神。
看來口口聲聲說不追著他,都是假的,都是吃醋而已。
如今他把人送走,什麼氣都沒了。
朱謙心里空落的那一塊總算得到了填補。
連著嗓音也添了以往沒有的,
“皇兄相邀,不得不去,一次宴會而已”
沈妝兒的憂漾在眼底,前世朱謙并未帶赴宴,并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也不知該如何未雨綢繆,正糟糟想著,男人眉眼近,瞳仁深如濃墨,
兩世夫妻,沈妝兒看他一眼便知他想做什麼,荑推在他膛,聲道,
“王爺,這是書房,外面有人呢”
猜你喜歡
-
完結13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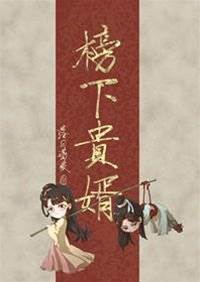
榜下貴婿
預收坑《五師妹》,簡介在本文文案下面。本文文案:江寧府簡家世代經營金飾,是小有名氣的老字號金鋪。簡老爺金銀不愁,欲以商賈之身擠入名流,于是生出替獨女簡明舒招個貴婿的心思來。簡老爺廣撒網,挑中幾位寒門士子悉心栽培、贈金送銀,只待中榜捉婿。陸徜…
46.9萬字8 7390 -
完結791 章
穿越后每天都在努力保胎
比起死回生更扯的是什麼? 是讓死人生娃! 莊錦覺得自己多年信封的科學世界觀完全被顛覆了,每天都徘徊在做個好人這件事上,要不然肚子里那塊肉就會流產,流產了她的屍身就會腐爛,腐爛她就完全嗝屁了。 好在原身有良心給她開了個天眼,方便她薅羊毛,看那位功德加身金光閃閃無比耀眼的小哥,絕對是個十世大善人,完全就是為她保命而存在的! 武都最野最無法無天世子爺:......
141.6萬字8 18598 -
完結183 章

繾綣
昭寧公主沐錦書,韶顏雅容,身姿姣好,是一朵清冷端莊的高嶺之花。 原爲良將之家僅存的小女兒,早年間,皇帝念其年幼,祖上功高,收爲義女,這纔有了公主的封號。 ** 夢裏回到那年深夜,皇兄高燒不止,渾渾噩噩間,他耳鬢廝磨,情意繾綣…… 忽一夢初醒,沐錦書紅着面頰,久久失神。 ** 時隔兩年,於北疆征伐的二皇子領兵而歸。 聽聞此,玉簪不慎劃傷沐錦書的指尖,滲出血珠。 再見時,他眉目深邃,添了幾分青年的硬朗,比起從前膚色黑了許多,也高大許多。 沐錦書面容淡漠如常,道出的一聲二皇兄,聲線尾音卻忍不住微顫。 他曾是最疼愛她的義兄,也是如今最讓她感到陌生的人。
28.2萬字8.18 3505 -
完結329 章

只有春知處
紀雲蘅發現她撿來的小狗瘋了。 見到她不會再搖着尾巴往她腿上蹭不說,給它帶的飯也不吃了,還不讓她摸,就藏在角落裏用一雙大眼睛戒備地看着她。 她只是無意間說了句:聽說皇太孫是個囂張跋扈的主。 就被小狗崽追着咬了大半天。 紀雲蘅氣得把它拴在院子裏的樹下,整夜關在外面,任它怎麼叫都不理,鐵了心地讓它好好反省。 誰知隔日一大早,就有個俊俏的少年爬上了她的牆頭。 ———— 許君赫原本好好的跟着皇爺爺來泠州避暑,結果不知中了什麼邪,每到日落他就會穿到一個叫紀雲蘅的姑娘養的小狗身上。 這小姑娘在紀家爹不疼也沒娘愛,住在一個偏僻小院裏,被人騎在頭上欺負。 這種窩窩囊囊,逆來順受之人,是許君赫生平最討厭的。 可是在後來張燈結綵的廟會上,許君赫來到約定地點,左等右等沒見着人,出去一找,就看到紀雲蘅正給杜員外的嫡子送香囊,他氣得一把奪下,“昨天不是教你幾遍,要把這香囊給我嗎!”
51.4萬字8 326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