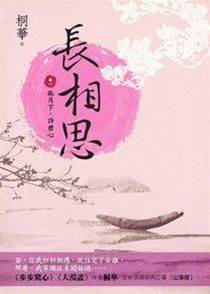《萬歲爺總能聽見我的心聲(清穿)》 第304章 番外——太后娘娘不想回宮
“皇額娘。”
一大早, 烏拉那拉氏就來給太后請安了。
宮奉上茶時,烏拉那拉氏接過茶盞,雙手奉給了太后。
太后烏雅氏看了眼兒媳一眼, 心里有些無奈,“在宮里你每日都不得松快, 好不容易到這里來幾日,何必每日來請安?”
“給皇額娘請安,是臣妾的福氣。”烏拉那拉氏帶著端莊的笑意, 說道。
太后知道自己這個兒媳婦的脾氣, 見這麼說就知道沒聽進去,索也不勸了。
也知道烏拉那拉氏不容易, 萬歲爺去歲封了后宮妃嬪們的份位,年貴妃、裕妃、齊妃等都晉了份位,后宮斗得跟烏眼似的。烏拉那拉氏為皇后, 實在不容易。
卯時時分。
太后和烏拉那拉氏一起用了早膳。
用過早膳后,烏拉那拉氏陪著太后出去散步消食, 避暑山莊春日天朗氣清、百卉含英, 松樹上麻雀啾啾聲不絕于耳,河堤旁楊柳翩躚,錦鯉雀躍不已,太后心大好, 命人取來魚餌喂魚。
烏拉那拉氏笑著陪著。
笑道:“皇額娘氣真是越發好了, 若是萬歲爺知道,肯定欣喜。其實若非萬歲爺忙于朝政, 也定要到避暑山莊來盡孝的。”
太后臉上出些笑意, 微笑著拍了拍烏拉那拉氏的手背, “本宮自然知道他的孝心, 朝廷上那麼多事,萬歲爺不來本宮是不會怪他的,何況他不來,有你陪著,本宮心里也是一樣用。你這回可得多住幾日再回去。”
烏拉那拉氏笑著道好。
可眉梢眼角卻有些愁意。
太后游玩了片刻,烏拉那拉氏便陪著回水芳巖秀。
太后也恤兒媳不易,讓回去好生休息。
Advertisement
烏拉那拉氏頷首稱是,等回去后,坐在梳妝臺前面卻是面憂容。
“皇后娘娘,您是不是為萬歲爺囑咐的事發愁?”
心腹喬嬤嬤替卸掉頭上凰咬珠步搖等珠釵,關心問道。
“可不正是。”烏拉那拉氏眉頭鎖,“萬歲爺囑咐本宮,要勸太后娘娘回宮里去住,好讓萬歲爺多盡盡孝心,可這話,本宮是真不知道該怎麼開口。”
來了幾日,幾番暗示宮里萬歲爺是如何想念的太后。
太后卻仿佛聽不懂一般,要麼就是笑而不語要麼就是像今日一樣打馬虎眼糊弄過去。
要說烏拉那拉氏也不是缺心眼,如何看不出太后不想答應這事?
但卻不得不提。
萬歲爺這麼多年也就麻煩這麼一件事,難道連這件事也辦不好不?
“娘娘,”齊嬤嬤心疼地替著肩膀,“依奴婢看,您倒是不妨直說,之后太后大答不答應,咱們再想辦法才是。總是這麼拖下去,可不是個辦法。”
烏拉那拉氏素來聽得進勸,齊嬤嬤這麼一說,思索片刻,也覺得有幾分道理,便有些坐不住,想立刻過去說這事。
但這會子才回來沒多久,要是這麼快回去,就顯得太過急切。
因此,烏拉那拉氏著子,等到黃昏時分,差不多了才過去提了這事。
太后聽了這話,心道可算是說出來了,笑了下道:“皇帝和皇后有這樣的孝心,本宮心里是高興的,但回宮去,本宮卻是不愿意。”
“??”
皇后愣了愣,素來沉穩的臉上頭一次出慌錯愕的神。
太后不覺得好笑,當初怎麼就沒覺得老四媳婦這麼好玩呢?
難道以為自己會不好意思拒絕嗎?
Advertisement
活到太后這個年紀,什麼都有了,是萬不愿意委屈自個兒的。
“皇額娘,您為什麼不愿意回?可是宮里哪里不好?”
烏拉那拉氏忙問道。
太后擺擺手,“宮里沒有不好,本宮不愿意回,是因為本宮在這里住的更開心罷了。”
烏拉那拉氏想了想,不答應就徹底沒有機會,于是只好答應。
太后臉上出笑容,對烏拉那拉氏道:“明日你換輕便的裳再過來,頭上珠釵也別戴太多。”
烏拉那拉氏疑地答應了,不明白太后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藥。
次日,烏拉那拉氏一早過來,穿了素紫旗服,頭上也只是戴著兩把金釵,太后瞧了微微點頭,命人傳膳,又對烏拉那拉氏道:“皇后等會兒早膳多用些,可有什麼想吃的?”
“臣妾今兒個倒是想吃縐紗小餛飩,”烏拉那拉氏道:“上回在您這里吃的餛飩特別好吃,跟宮里頭的味兒不太相同。”
太后人上一碗餛飩,聽烏拉那拉氏這麼說,笑著解釋道:“避暑山莊這邊的餛飩做法是善貴太妃指點過的,自然和宮里不一樣。你既吃,回頭人把做法寫了,讓宮里也照著做就是。”
“多謝娘娘疼臣妾。”烏拉那拉氏出些笑意。
娘家人時常擔心太后娘娘子冷淡,不好說話,其實,在烏拉那拉氏看來,太后娘娘子冷是冷了些,可卻比尋常婆婆更明事理好說話,也不拿什麼規矩來教兒媳婦。
因此,無論是剛結婚那會兒,還是現在,烏拉那拉氏都沒經歷過婆媳矛盾。
縐紗小餛飩送了上來,一個個像小金魚一樣,湯底清澈,拿豬大骨熬的湯底里加了紫菜、蝦皮、蔥花、蛋皮,湯鮮無比,上面撒的蔥花更是添了幾分賣相,這碗縐紗小餛飩可謂是香味俱全。
Advertisement
烏拉那拉氏沒忍住,等回過神來,一碗縐紗小餛飩已經吃的干干凈凈。
額頭上熱出細汗,有些不好意思。
太后笑了笑,讓人給夾了個牛鍋,“多吃些才是好事。”
烏拉那拉氏道了謝,總覺得太后的笑容別有深意。
婆媳倆用了早膳,烏拉那拉氏以為太后要去散步消食,也跟著去,不曾想,這回卻是走了其他方向。
心下困,走著走著,眼睛卻是映一片翠綠,不遠赫然是幾畝菜地。
菜地旁邊還著幾塊板子,離得遠了瞧不清上面寫的什麼。
菜地里還有人。
烏拉那拉氏瞧著那人形,只覺得悉,待要琢磨是誰時,那人卻回過頭了,朝們這邊出個笑容。
“宜太妃娘娘?!”齊嬤嬤驚呼出聲,隨后意識到自己失態,連忙閉上低下頭,可卻怎麼也忍不住拿眼睛去瞧。
“太后,您今兒個可來得晚了些。”
宜太妃手里拿著水瓢,對太后笑著說了句,又看向烏拉那拉氏:“皇后娘娘也來了?”
太后道:“今日來陪本宮。”
宜太妃將信將疑,皇后娘娘是能干這種活的人嗎?
太后招呼幾乎失神的皇后去旁邊搭好的草棚下戴上袖套,換了鞋,花盆底可不能在田地里走。
等皇后回過神來,已經一手提著水桶,一手拿著水瓢在菜地澆水了。
菜苗綠汪汪,春天的韭菜長勢極其喜人,迎面春風吹拂,水珠順著葉子滾落,不知怎地,烏拉那拉氏的心好了不。
等按照太后的意思澆完了水后,太后又過來遞給一雙手套,“咱們今兒個還要除雜草,我教你怎麼認那些雜草。”
烏拉那拉氏看著手套,遲疑片刻。
太后催促道:“快戴上啊,你這孩子別是想徒手拔草吧,我告訴你有些草可銳利著呢,一拔能給你手心拉個大口子。”
齊嬤嬤等人在旁邊都是言又止。
皇后娘娘可是一國之母,怎麼能做這些活?!
便是親蠶禮,那也不過是走個形式罷了!
烏拉那拉氏遲疑片刻,還是把手套給戴上了。
結果忙完了除草,又跑去摘櫻桃。
櫻桃樹上碩果累累。
太后語氣中帶著幾分得意地挑揀著剛從樹上摘下來的櫻桃,對皇后道:“這櫻桃樹可是我和宜太妃娘娘一起照顧的。”
皇后臉上出驚訝神,瞧了下,樹上竟然真掛了個牌子,上面寫了太后和宜太妃,而旁邊的櫻桃樹、杏樹也都各有各的牌子。
忍不住問道:“皇額娘,你們怎麼還把這些樹給分了?”
難不是圖這些果子不?
宜太妃笑道:“不分誰能認得出哪棵樹是誰的,這樣比賽怎麼能出果?”
“比賽?”
皇后越發覺得稀奇了。
太后解釋道:“原先是去年年初善貴太妃帶著安妃種田種樹,我們瞧著也心,再說這勞作也對子骨有益,便都跟著學起種田種樹,順帶比賽,這幾棵樹倒不是我們種的,只是我們先拿來練手照料罷了,不過,今年這櫻桃樹也比往年結的果子更多了。”
說到最后,臉上顯然出自豪和得意的神,“雖輸給了宜太妃們的櫻桃樹,可論結的果也是這片果樹里數一數二的。”
皇后這才明白這其中緣由。
不由得覺得好笑,心里卻也生出幾分羨慕。
太后挑揀出的櫻桃被送下去洗了。
一行人尋了附近的曲水荷香亭,到亭子里坐下休息。
這亭子所的位置極好,背靠假山,奇石環繞,流水淙淙,櫻桃洗干凈后送上來了,太后挑了個最大的給了皇后,“你嘗嘗。”
皇后道謝后接過手,嘗了一口,只覺得味道酸甜可口,水飽滿,比起貢品滋味更好。
再加上是們辛苦摘下來的,更添了幾分喜。
“剩下的櫻桃,本宮尋思著回頭摘下來釀櫻桃酒,等酒釀好了,也派人送去給你們嘗嘗。”
太后臉上出笑容。
臉上的快樂和怡然自得,是皇后先前在宮里從未見過的。
猜你喜歡
-
完結204 章
神醫世子妃
穿越成首富嫡女,又擁有一身醫術,遊遊山,玩玩水,卿黎表示日子過得還不錯. 一道賜婚聖旨,將這份平靜打破,衆人譁然之際,她只淡淡一笑:嫁就嫁,到時討封休書,照樣海闊天空. 只可惜,滿打滿算,依然行差踏錯,步步偏離原軌. 卿黎扶額一嘆: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既已身陷局中,何不反客爲主,奪了這主導權!
53.8萬字7.82 56214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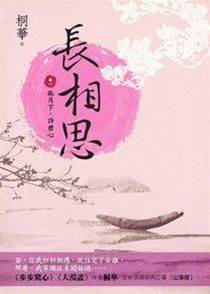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57 -
完結466 章

丑妃撩人:王爺請接招
一道賜婚圣旨,兩人從此糾纏不清。她霍兮容這麼多年費盡心思,都是為了躲避皇家之人,怎麼到最后竟功虧一簣。本以為憑借自己的‘美貌’,即使王爺不與自己合離,兩人也會相敬如賓。可如今是什麼情況,這頻頻護自己、秀恩愛的男子,就是傳說中滿身戾氣的璟王嗎?但,既然木已成舟,自己已坐上王妃的寶座,那她便涅火重生,叫天下眾人皆不敢欺她分毫!
88.2萬字8 3792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