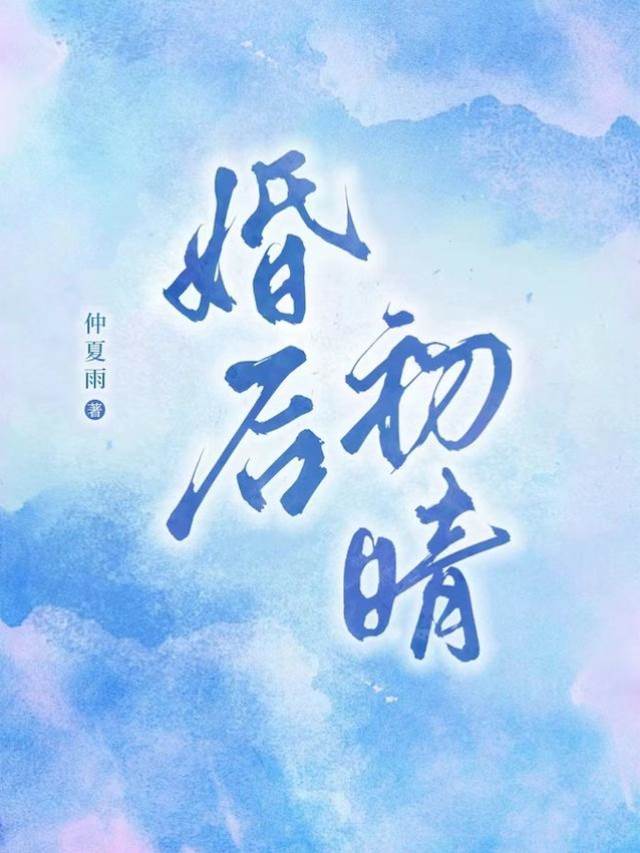《君心》 第 32 節 褪丹青
我抿了抿,看著蕭景策:「你回去吧。」
「回哪里去?我自然要與夫人同去北疆。」
蕭景策眨了眨眼睛,
「平王府有玄羽帶人鎮守,我雖不能上陣殺敵,但這些年來讀了這麼多兵書,總能給夫人做個軍師。」
「可邊疆苦寒,此行兇險,你的……」
他輕笑一聲,打斷了我憂心之言:「有夫人在一日,便能護我一日周全,不是嗎?」
15
深冬時節,我與蕭景策一路快馬加鞭,抵達北疆。
起先,即便有虎符在手,平軍也并不服我。
我當著他們的面,徒手劈碎了一塊重逾數百斤的巨石,才算勉強鎮住了他們。
回到房中,蕭景策便微微側過頭,沖我笑了:
「原來從前在京城時,清嘉一直在藏鋒,可算是對我留足了面。」
我抿了抿,忽地探出,揪住蕭景策襟,吻住他。
輾轉反復,他被我親得不已,連眼尾都泛起一抹紅。
「夫人……」
他眸幽深地著我,那雙山泉般清澈又冷靜的眼睛里,漸漸有火焰燃起,「夫人,別撥我,我不住。」
我閉上眼睛,將下抵在他肩窩,輕聲道:「蕭景策,謝謝你。」
從前在姚家,我一直過著萬分不適的日子。
不只是姚清婉,嫡母也很會對付我。
說姚家一向勤儉,既然我力氣大,府中的柴火便都給我來劈。
這對我來說不過是小事一樁,因而發覺為難不到,便又尋些旁的法子。
比如數九寒天,命我跳湖中為撈回掉落的手帕;比如在做給我的中,細細一排牛細針;比如用我小娘的安危迫我,替酷配置毒藥的姚清婉試藥。
似乎子在閨閣,嫁人后又困在后宅,連眼界都被消磨至不可見的地步。
Advertisement
那并非我想過的日子,因此在京中時總是千般不適,每一刻都有萬重枷鎖束縛,舉步維艱。
如今,到了北疆,總算天大地大,再無拘束。
三日后,我帶領平軍與北羌人在半月關外一戰。
平軍本就是上一任平王帶出的一支奇兵,又因這些年來鎮守邊關,被北疆凜冽的風雪磨礪出一銳利的森寒。
我提著一柄長刀,一馬當先,連挑北羌三名大將,初戰大捷。
雖然勝了,衛云朗的臉卻十分難看。
我越得軍心,他日后想要接管平軍就越困難。
蕭景策聽了我說的話,挑了挑眉:「夫人不必擔心,如今戰事吃,他暫時不敢耍什麼手段。」
他讀兵書,于兵法一道的理解上要遠勝于我,于是我與蕭景策形了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
我領軍征戰,他布局謀劃。
不足兩月,便收回五座北疆城池,捷報頻頻傳回京城,連帶著衛云朗的神,也一日比一日沉。
他引以為傲的天才年的環,在我面前被悉數澆滅。
年關將至時,北羌人已退至草原界的斷風關。
我與蕭景策的第一個新年,便是在北疆度過的。
除夕夜,他溫了酒,笑笑地舉杯祝我:「將軍天生就該建功立業,萬古流芳。」
這兩個月的戰場拼殺磨礪下來,我上染了氣,比起在京城時束手束腳的模樣,何止肆意了百倍。
目掠過蕭景策執酒杯的手,指節修長,分外漂亮,許是因著喝了酒的緣故,他清俊出塵的臉上多了幾分。
我覆住他的手,就著這個姿勢將杯中酒一飲而盡,笑了一下:「軍師亦是。」
夜深時分,我在簡陋屏風后沐浴,不知不覺倚著浴桶邊緣睡了過去,直到一輕的力道落在我發間,將我自夢中喚醒。
Advertisement
我啞著嗓子,懶洋洋地問:「咦……蕭軍師此番前來,所為何事?」
蕭景策我漉漉的頭發,笑意輕淺又勾人,低聲道:「自然是來為將軍侍寢。」
那溫熱的指尖沿我脖頸一路往下,沒水面漣漪,又點起燎原烈焰。
北疆落雪的除夕夜里,我與蕭景策房中盛開了
第一個春天。
16
開春時節,最后一戰終至。
在蕭景策出其不意卻又妙絕倫的布局下,我領兵大敗北羌軍,對方退至斷風關外。
領頭的二皇子向我,目刻毒:
「姚將軍一介流卻有將才,金某很是佩服。只是你此生,怕是都不能離開北疆了。」
「今日之仇,我記下了。來日見你楚國之軍,必殺之而后快。」
他在一小支心腹之軍的掩護下,匆忙撤退。
我握韁繩,一聲冷笑,高聲厲喝:
「你北羌已然大敗至此,難道我還會放虎歸山?其他人清理戰場,收拾殘局,十三輕騎小隊,同我一起追過去——」
我的聲音落在北疆初春凜冽的風中,聚攏了一瞬才四下飄散。
「斬草除。」
我帶人追了三百余里,北羌二皇子的心腹一個個被殺掉,到最后,只剩我策馬追著他,一路奔草原深。
幾步之后,衛云朗跟著我。
二對一,何況對方又是強弩之末,原本該是板上釘釘的勝利。
然而在我提刀刺向北羌二皇子的一瞬,衛云朗忽然調轉刀鋒,重重砍向我下馬匹的前。
駿馬一聲慘烈嘶鳴,跪倒在地。
我跟著往前傾,銳利劍尖迎面向我刺來,堪堪沒心口半寸。
也是這個時候,斜里忽然一支寒凜然的長箭飛來,用力之大,竟然將那柄劍從中斷!
Advertisement
我得了息之機,飛下馬,高高揚起手中長刀,用了十分力氣。
北羌二皇子的首分離,高高飛起的頭顱之上,還殘留著驚懼和不敢置信的表。
爾后我猛然轉,從背后取下長弓,瞄準,利落地搭弓箭。
長箭自逃離的衛云朗后心穿過,他從馬上栽倒下來,滾落在草叢之中,沒了聲息。
急促的馬蹄聲漸近,一轉眼便停在我面前。
蕭景策翻下馬,面倉皇,步履踉蹌地到了我面前,死死盯著嵌我口的那半截劍尖。
他在我面前,從來都是運籌帷幄的模樣,縱然從前在京城時命懸一線,亦是萬般從容。
我從未見過蕭景策這樣失態。
懊悔和痛惜在他眼底掀起巨大的風暴,聲音被風撕扯著,滿是驚惶。
「清嘉,對不起,我來遲了……」
我咧了咧,抬手將劍尖拔出來,輕聲安他:「沒有遲,蕭景策,你并沒有來遲。」
見他不肯信,我只好解了騎裝,翻開襟,將那枚荷包掏出來:
「看,我放在這里,珍而重之地藏好,原本是想等這一戰贏了,就送給你的。」
那枚繡工拙劣的荷包,卻替我擋下了這生死一劍,令我只了一點皮傷。
只可惜,上面辛辛苦苦繡好的鴛鴦和月亮,已然線散,不形狀。
他盯著我,見我赤心口只有一點輕淺紅,顯然是真的并未什麼重傷,終于放下心來。
「看吧,我就說——」
蕭景策結了,猛地上前一步,將我死死抱住。
用力之大,甚至讓我覺到輕微痛意。
他附在我耳邊,嗓音微微沙啞:
「方才那一瞬間,我以為你傷在他劍下,險些懊悔至死。我想我不該為一己私心,將你置于這般危險的境地,若是你死在北疆戰場,我也定會與你合葬于此。」
「清嘉,我真的害怕,怕失去你。」
他難得示弱,這聲音里帶著劫后余生的慶幸。
糙的騎裝表面帶著初春未散的料峭寒意,蹭在我肩頭。
天漸漸暗了,天上月落下來,鋪陳在滿地草葉之上,融在這個擁抱的每一寸隙間,拉扯出一片寒冷中氤氳的曖昧。
我還未反應過來,便有一滴溫熱的意滴落在肩上。
細的草尖刺著后背,微微有些不舒服。
我卻顧不得許多。
「蕭景策,你一直在騙我……」
我一邊兇狠地吻他,一邊用發抖的聲音說,
「你能騎馬一路追來,亦能搭弓箭,一箭斷他的兵刃——你分明并非纏綿病榻,也絕不到行將就木的地步,又為何要裝病這麼多年。」
「若是不病,便是死,清嘉,我沒有第二條路。」
他頸線繃,包容地承一切,
「如今這樣,不也很好嗎?你有驚世之才,自然該被天下皆知。而我做你后軍師,助你守衛萬里河山。」
「姚清嘉,我要你青史留名,而我之名綴于你之后,已是心滿意足。」
這一夜仿佛格外漫長,遼闊草原上,曠野星河下,回程我與蕭景策同乘一匹馬。
他寬大的披風裹住我,顛簸間抑暗流,唯有那被披風包裹的方寸之地間,是我們二人難得的歡愉。
17
北地收復,副將衛云朗因勾結北羌人,被就地決。
而我與蕭景策帶領兩萬平軍,班師回朝。
一路上,百姓夾道歡迎,平軍沉寂多年的赫赫威名,終于歸來。
抵達京城的第二日,天子于宮中設宴接風。
我上還帶著幾分北疆未褪的凜冽寒氣,進殿時不知為何,高高在上的天子竟然盯著我,恍惚了一瞬。
「姚卿巾幗不讓須眉,朕自當敬你一杯。」
回過神來,天子高舉酒杯,遙遙與我相。
爾后變故陡生。
他喝下那杯酒,須臾便七竅流,倒在地。
殿大間,三皇子猛然起,拔出一旁衛軍上的長劍,劈手將面前的桌案一分為二,爾后高聲喝道:「肅靜!這般大,何統!」
六皇子一聲冷笑:「父皇才咽了氣,三哥這便等不及了嗎?真是好大的威風!」
七皇子亦是起,在幾個心腹手下的掩護下,警惕地盯著二人。
這三位皇子,恰巧便是爭奪儲君之位最有可能的人選。
我神冷峻地后退一步,想將蕭景策擋在后,他卻反手將我護住,低聲道:
「夫人戰場辛苦已久,這一仗,還是我來吧。」
那一晚,楚國皇宮燈火通明地亮了一整夜,幾近流河。
三位皇子分庭抗禮,手中的勢力幾乎不分伯仲。
僵局之勢時,還是平王蕭景策帶領三千平軍出現。
誰也沒想到,一直以來都表現得極不對付的三皇子與蕭景策,竟然聯手破局,了最終勝者。
天蒙蒙亮時,蕭景策渾染,拎著一把長劍,搖搖墜地站在了我面前。
不待開口,便偏頭吐出一口來。
我眼睫了,在初升的日中看向蕭景策:「你又騙了我。」
「……是。」
「你與三皇子,從來沒有不對付過。」
「是。」
蕭景策了兩口氣,面上有痛楚之一閃而逝,「我與他,是同母異父的親兄弟。」
「先帝心儀我母親多時,卻因有赫赫戰功,忌憚占了上風。一直以來,他都想折了的羽翼,收回的兵權,將囚在深宮。我母親與他幾番博弈,生下我弟弟后,好不容易獲得一線生機。」
「因為南州有,他需要我母親前去平。」
整整九年,蕭景策的母親將楚國的大好河山一一收復,在民間威深重,先帝心中的忌憚卻愈發深重。
他既,又妒忌一介子,竟有這等驚世之才。
最終,在蕭景策的母親又一次表明不愿屈服、不愿長留在后宮時,他便殺了,又瞞下三皇子的世,隨便尋了個宮封作他的母妃,令他與蕭景策反目仇。
后來三皇子偶然得知真相,暗中聯系到蕭景策,這才定下來表面離間的漫長計劃。
「我母親死后,他仍不肯罷休,將當初的舊部一點點鏟除,令平軍的威名漸漸沒落,甚至十年后,京中再無人知曉我母親的功績與姓名——名為蕭卿玉,千百年后史書落筆,也該有的名字。」
天邊新日升起。
從蕭景策的寥寥數語中,我已經能聽出那名為蕭卿玉的奇子,跌宕起伏卻又傳奇燦爛的一生。
因著一個君王的妒忌之心,在塵埃中困頓許久,如今終于得以昭雪。
「我并非故意不告訴你,只是一切并未塵埃落定,何況王敗寇,若是這一仗是我與他敗了,你既對此不知,又有戰功與兵權在,便是即位的是旁人,也不會將你定罪。」
我沉默片刻,淡淡道:「你說過,我若死在北疆,你會與我合葬。」
「若你死在京城,我亦會同你殉——蕭景策,你本就不信我的心意。」
18
新帝即位,一切塵埃落定。
蕭景策仍為平王,只是平軍已在我麾下。
而我封嘉遠將軍,居正二品,另辭府邸居住。
衛云朗背負著通敵之罪死,周衡也好不到哪里去。
新帝登基后,他父親很識趣地告老還鄉,他也了一介庶民。
輿論徹底扭轉,京中眾人口中,我從之前那個心狠手毒的俗子,變了名震天下的第一將軍。
回府后,我娘見了我,忙不迭地迎上來,仔仔細細檢查一遍,確認我并未傷,才總算放下心來。
只是,我與蕭景策又開始了冷戰。
事傳到宮里去,剛即位不足月余的新帝甚至專程來勸說我:
「姚將軍莫怪,瞞一事是出自朕的意思,與哥哥無關。」
「家事而已,便不勞陛下費心了。」
我起,跪下行禮,「臣想為家母請封誥命。」
從前見了蕭景策便橫眉冷對,冷笑連連的新帝和悅地說:
「小事一
樁,朕等下便回宮擬旨,封姚將軍的母親為正三品誥命。」
我很滿意。
畢竟我爹做了大半輩子,也不過堪堪從三品。
而且因為姚清婉的緣故,他如今又被降了職,連同姚家也一并沒落了。
過去在姚家那些被折磨、被戲弄挖苦的回憶,如今想來,也的確只剩下回憶而已。
離開前,他忽然想起什麼,忽然又折返回來:
「對了,姚將軍那位嫡妹因意圖謀害皇后腹中的孩子,如今被朕關在天牢之中,不日便要賜死,姚將軍可還有什麼話要同說的?朕可以安排你見一面。」
他說的,是姚清婉。
自我見過更遼闊的天地之后,那點后宅的私手段,在我看來便愈發無趣,甚至不值得多耗費一心神。
于是平靜地回了句:「不必見了。既然有謀害之心,殺了便是。」
新帝點點頭,終于離開。
他走后,蕭景策又一次出現,立在門口,可憐兮兮地著我。
可惜,我已知曉他從前種種病癥都是裝出來的,心毫無波,只是面無表地著他。
「這兩日我回憶舊事,才算反應過來。上一次所謂的投毒和刺殺,都是你安排好的吧?目的就是為了讓我心?」
蕭景策沒有出聲,顯然是默認了。
我冷然道:「你下手也夠狠,不怕真的死在那一劍下嗎?」
蕭景策抿了抿,輕聲說:「你再也不肯原諒我了,是嗎?」
說不原諒,好像也不至于。
我只是有點生氣,心又不自覺地泛出一點酸,像是某些難以用確切言語表述的心事。
于是我暫時從平王府搬了出去,住回自己的府邸。
一連半月,只要是我不上朝、不去校場的日子,蕭景策便天天往這邊跑。
我不許門房給他開門,他便站在門口癡癡等候,引得路人駐足,議論紛紛。
沒辦法,我只好又把人放了進來。
我低頭研讀兵書,蕭景策就在旁邊笑瞇瞇地著我,仿佛一點都不覺得無聊。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到了我生辰那日。
我娘一早就開始辦,指揮廚房里做好菜,府張燈結彩,紅艷艷的燈籠掛了滿院。
從前在姚家時,因為份微賤,嫡母不許我過生辰,我娘能給我煮一碗長壽面,已是難能可貴之事。
「那次我想在你的面里加些新鮮的魚蝦,被小廚房的人發現了,稟報上去,那些人當著我的面,將碗里的東西倒給了府外墻的野狗。」
提及舊事,眼中便覆了層瑩瑩淚,「如今你已年滿十八,才算過了個像樣的生辰。」
我安:「娘親不必太難過,日子總是越過越好的。」
說話間,蕭景策來了,見狀二話不說,挽了袖子便開始幫忙掛燈籠。
一直到傍晚,天暗下來,初夏的暖意已經飄散在風中。
我多喝了幾杯酒,暈暈沉沉間,見我娘退了出去,還關好房門,將房間留給我與蕭景策。
一修長的手指在我面前晃了晃,在我迷蒙的目中勾了勾我下:「還在生我的氣嗎?」
「我沒有……生你的氣……」
半醉半醒間,我腦子有些混沌,干脆將心中的話傾吐而出,
「我只是不明白,為什麼你明明那麼怕我死,卻又將自己的命看得那樣不重要……若是那毒并未被抑制住呢?若是我沒擋下那一劍呢?還有,為什麼不告訴我你和陛下的真正關系,若你死了,我真的能心安理得獨活下去嗎?」
蕭景策沉默半晌,終于開口,嗓音有些然:「因為……我不敢去想那種可能。」
「什麼可能?」
「清嘉,我始終怕你不喜歡我,與我這些日子的相,不過是你之前所說的易。可我又不敢直接問你,怕得到的,是某些我不能承的答案。見你對我的臉、我的還算興趣,我只好用它們留住你。」
他說得十分可憐,醉意上涌,我腦子里混混沌沌,直覺有哪里不對勁,卻又說不上來。
「你為何會覺得我不喜歡你?」
「因為你并未說過。」
我沒說過嗎?
我努力地回憶了一下,似乎真的是這樣。
一直以來,都是蕭景策在毫無遮掩地向我傾表意。
我唯一說過的,也不過只有新婚之夜那一次演技拙劣的試探。
于是我張了張:「我當然喜歡你啊。」
「是嗎?」一溫熱的氣息漸漸湊近了我,響起來的聲音里帶著強烈的哄意味,「再說一遍。」
「我當然喜歡你啊,蕭景策。」
眼前天旋地轉。
紅燈籠里的燭出來,深深淺淺地穿過幔帳,落在我與蕭景策上。
我努力睜大眼睛,著面前的蕭景策。
一直以來,他都在我面前示弱慣了,如今終于現出幾分難得的強,引我共舞。
燈籠太紅了,紅得像是又一個新婚之夜。
不同的是,這一次我和蕭景策并未如從前那樣,命運在莫測的局勢中飄搖不定,反倒有了可以掌握在手的、難能可貴的力量。
我張口,重重咬住他肩膀。
「不許再不拿自己的命當一回事了。」我惡狠狠地說,「若是再有一次,我便與你和離,另尋新歡。」
「不會了。」
他用濡的吻輕輕安斷風關那一戰留給我的傷口,「蕭景策這條命,從此是你的了。」
(尾聲)
后來我與蕭景策又辦了一次婚禮。
極為盛大,幾乎邀請了滿京城有頭有臉的人家。
他說,是因為上一次親時,他要維持將死之人的人設,并未同我拜堂,因而留下憾。
好在這一次,是我一喜服,端坐在高頭大馬之上,去平王府將嫁華麗的蕭景策娶回了將軍府。
皇上甚至帶著皇后前來觀禮,來自東北的皇后忍不住嘆:
「這……平王與嘉遠將軍,玩得花啊。」
再后來,蕭景策拿出之前那枚救下我一命的荷包。
我著那上面散不型的線,有些心虛:「要不我再給你繡一個吧?」
「不必,這個就好。」
蕭景策說著,輕笑一聲,竟又從懷里拿出一枚繡工萬分巧的荷包,遞到我手上。
我很震驚地看著他:「你繡的?」
「自然。」
他笑得很是賢惠,
「將軍在外奔波,自然需要荷包裝好件,我閑來無事,便為你繡了一個。」
很快,平王蕭景策賢良淑德的名聲,漸漸傳遍了整座京城。
那天夕西下,我從校場出來,便看見他遠遠地騎在馬上,沖我招手。
「清嘉。」
金紅的芒倒映在他眼中,將那里面的笑意染一片逶迤的火焰。
我握韁繩,策馬,向我的歸而去。
猜你喜歡
-
完結173 章

甜寵!京圈白月光恃寵而嬌
【豪門千金X富家少爺】【皮膚管理中心老板x陸氏集團總裁】現代言情 豪門總裁 豪門世家沈若琪從小在蜜罐裏長大,有點嬌氣的富家千金。陸璟宸一個有權有勢有錢有顏值的集團總裁。***“沈若琪我喜歡你,你願意做我女朋友嗎?”在一起後陸璟宸做的第一件事:發朋友圈文案【我的】沈若琪看到後在下麵評論【你的】【雙潔 甜寵 嘎嘎甜】
21.1萬字8 15515 -
完結251 章

深度曖昧
《清冷絕豔旗袍美人X見色起意京圈太子爺》《成人愛情 頂級曖昧 極致拉扯 肆意纏綿》周江野說一見鍾情都是瞎扯淡,那叫見色起意。然而周江野在賽車場第一次見鹿苑時他何止是見色起意,一眼便淪陷,一見便鍾情。鍾的是她,情……情難自控。—在一次機車比賽後,周江野取下頭盔,扣著一身穿白色淡雅旗袍的女人吻的難舍難分。女人身材曼妙,熱烈回應。何止是他一眼淪陷。某天,在哥哥的婚宴上,周江野黑眸炙熱的盯著身側的清冷絕豔的鹿苑:“我們結婚吧。”鹿苑眼睫微顫,側眸漫不經心道:“有感而發?”周江野笑了笑,垂眸看著她的左手無名指:“心之所向。”*海底月是天上月,眼前人是心上人。
47.6萬字8 12136 -
完結156 章

穿成侯門寡婦後,誤惹奸臣逃不掉
【雙c 傳統古言】沈窈穿越了,穿成了丈夫剛去世的侯門新鮮小寡婦。丈夫是侯府二郎,身體不好,卻又花心好女色,家裏養著妾侍通房,外麵養著外室花娘。縱欲過度,死在了女人身上……了解了前因後果的沈窈,隻想著等孝期過了後,她求得一紙放妻書,離開侯府。男人都死了,她可不會愚蠢的帶著豐厚的嫁妝,替別人養娃。 ***謝臨淵剛回侯府,便瞧見那身穿孝服擋不住渾身俏麗的小娘子,麵上不熟。但他知道,那是他二弟剛娶過門的妻子。“弟妹,節哀……。”瞧見謝臨淵來,沈窈拿著帕子哭的越發傷心。午夜時分,倩影恍惚,讓人差點失了分寸。 ***一年後,沈窈想著終於可以解放了,她正要去找大伯哥替弟給她放妻書。沒想到的是,她那常年臥病在床的大嫂又去世了。沈窈帶著二房的人去吊唁,看著那身穿孝服的大伯哥。“大伯哥,節哀……。”謝臨淵抬眸看向沈窈,啞聲說道:“放你離開之事,往後延延……。”“不著急。”沈窈沒想到,她一句不著急, 非但沒走成,還被安排管起侯府內務來。後來更是直接將自己也管到了謝老大的房內。大伯哥跟弟妹,這關係不太正經。她想跑。謝臨淵看著沈窈,嗓音沙啞:這輩子別想逃,你肚子裏出的孩子,隻能是我的。
31.5萬字8 9189 -
完結313 章

踹掉渣男閃婚!被神秘老公寵的麵紅耳赤
江若曦愛了付明軒十年,為他犧牲一切,斷絕親情,成為一個人人嘲笑的大舔狗。可他,卻在她被綁架後,不痛不癢的冷嘲一句,“撒謊要有個限度,我很忙,不要再來騷擾我!”後來,江若曦慘遭撕票,死無葬身之地。重生後。她腳踹渣男,手劈白蓮,瀟灑扔出一份離婚協議。卻不料,前夫先生幡然醒悟,玩命追妻。而前世那個疑似殺害她的綁匪頭目,竟秒變瘋狂追求者,一哭二鬧三上吊,隻為做她的最強保護神!付渣:“老婆,求你了,咱們複婚好不好?”夜狗:“你好前輩,不好意思,曦曦是我的!”
28.3萬字8.18 39186 -
完結14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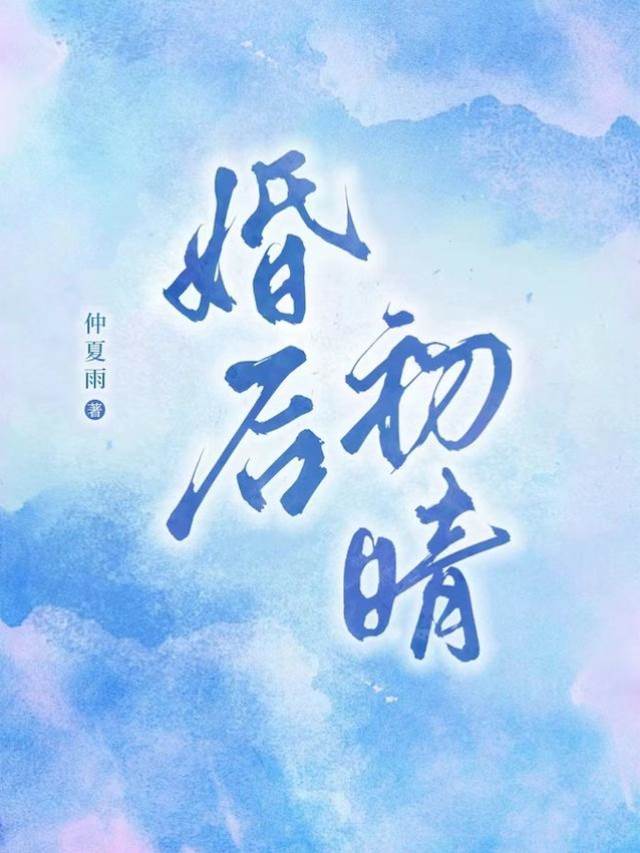
婚後初晴
沈頤喬和周沉是公認的神仙眷侶。在得知沈頤喬的白月光回國那日起,穩重自持的周沉變得坐立難安。朋友打趣,你們恩愛如此有什麽好擔心的?周沉暗自苦笑。他知道沈頤喬當初答應和他結婚,是因為他說:“不如我們試試,我不介意你心裏有他。”
27.2萬字8 4900 -
完結249 章

美強慘重生后,被病態容爺纏哭了
【重生➕女強➕馬甲➕真假千金➕甜寵➕萌寶➕絕不受委屈】上一世,虞婳是個真千金,吃了十八年苦才被接回家,結果爹娘以及四個哥哥都只疼愛假千金虞江月,將她視作草芥。 連她第一個心動男人,也是虞江月的青梅竹馬。 最后,她甚至被迫嫁給A國人人懼怕的大魔頭容硯之,懷孕生子,受盡折磨。 終于,虞婳黑化了,變成惡女,處處針對賣慘的虞江月,覺得是她搶走了自己的人生,給人一種不顧別人死活的瘋感。 什麼豪門老公,天才兒子,她統統不要,每天只想著讓虞江月不好過。 可令她沒想到的是,兒子隨了老公,越長越歪,又壞又瘋,長大后把她這個不稱職的媽搞死了。 上天許是看她可憐,讓她重生回到了五年前,然而這個時間段,她已是被萬人唾棄的毒婦。 不過沒關系,重活一世,她只顧自己爽,親情?愛情?都給她滾一邊去! 打臉虐渣,樣樣來。 手握無數馬甲底牌,爛命一條就是干。 - 虞婳表示重來一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容家父子倆,離婚協議一甩,先前討厭她的兒子抱著她不讓她走,一向冷峻矜貴的丈夫也只是說:“支持你做的任何決定。” 然后轉身就要開槍自殺。 OK,虞婳認命!這輩子還是得跟容硯之捆綁在一起。 容硯之:虞婳,我愿做你最忠誠的愛人
44.5萬字8 1051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