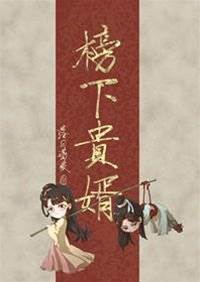《重生后我做了皇后》 第 137 章 第 137 章
攻破京城的次日,盛長樂母子便被接進了皇宮跟徐孟州匯合。
宮里此刻已經打掃清洗得干干凈凈,一塵不染,一如既往的富麗堂皇,若不是空氣中還彌漫著硝煙和腥的氣息,恐怕毫都察覺不出昨夜經歷了何等的腥風雨。
盛長樂進大殿時候,正瞧見徐孟州赤著上,上多纏著紗布,旁邊秦艽在給他包扎傷口,地上還有一堆沾滿鮮的紗布被清理出去。
待包扎好傷口,秦艽遣退出去之后。
立即迎了上去,坐在徐孟州邊,滿目擔憂的著他,“傷得重麼?”
徐孟州攬過的肩膀,著的手,若無其事的模樣,“皮外傷而已。”
盛長樂都親眼看見那皮開綻的傷口了,才不相信只是皮外傷!
不過盛長樂都不嘆,徐孟州還真是藝高人膽大,支闖皇宮這種事都干得出來,都快把嚇死了,只怕事不功,徐太后當真把他腦袋給割下來。
上回在城的事發生之后,李元璥負重傷,逃回京城,盛長樂母子則跟隨徐孟州去了西京,母子倆一直隨軍而行,不曾離開徐孟州半步。
后來盛長樂聽說李元璥重傷不治駕崩的消息,得知他就這麼死了,心下還稍微嘆,那一瞬間好像也沒那麼恨李元璥了,畢竟他這輩子也沒那麼罪大惡極。
特別是在城的時候,盛長樂還以為孩子落到李元璥手里必死無疑,卻沒想到,李元璥說不想再做傷害的事,只要聽話,便不殺孩子。
李元璥駕崩之后,徐太后便扶持著小皇帝垂簾聽政,徐孟州則帶兵攻打京城。
原本徐太后用計,想串通靖王在徐孟州背后捅刀子,還好,徐孟州察覺出來不對,設下圈套將靖王反殺,還順便將計就計,偽裝靖王進宮進獻人頭,派大軍尾隨突襲。
Advertisement
若不是徐孟州坦白有五哥在宮里接應,盛長樂死活都不肯讓他單獨進宮的。
好在計劃順利,現在大軍順利攻下鎬京,大片江山收囊中,徐孟州也準備在鎬京正式稱帝。
徐孟州竟然當真要做皇帝了,想一想便讓人心澎湃,激難耐。
片刻后,盛長樂才猛然想起一件要事,趕忙詢問,“太皇太后現在何?”
攻下皇宮之后,徐太后便被囚起來,徐孟州到現在也沒去看過。
盛長樂又問,“那,你打算如何置?”
徐孟州看向盛長樂,道:“自然是由你置。”
盛長樂癟,“我可不敢,那是你姐姐,若是我置得不妥,你將來怪我怎麼辦?”
徐孟州干脆利落道:“我怎會怪你?當初我被得離開京城之時,便已經一刀兩斷了,昨日還想取我人頭,就算你不出面,我也不會留半點面。”
盛長樂想了想,確實有些賬,應該找徐太后清算一下了。
*
過雕花窗戶進屋,可見一名錦華服,模樣狼狽的婦人,正抱著個一歲多的孩子,坐在屋里榻上。
正是徐瓊華,抱著懷里的麟兒,在孩子耳邊喃喃自語,也不知在說些什麼。
現在,只剩下麟兒了……
直到房門“吱呀”一聲被人推開,打破了屋里的寂靜。
徐瓊華尋著聲音看去,就見是盛長樂,著珠翠羅綺,態盈盈的走了進來。
已經有一年多時間不見,比起去年,現在的盛長樂因為剛生完孩子不久,紅滿面,態盈,□□拔,一天的氣質撲面而來,人眼前一亮。
徐瓊華一看見盛長樂,頓時面鐵青,氣得中泛起一腥味。
Advertisement
想方設法要除掉的人,如今卻依舊春風得意的站在面前,人家不僅好端端活著,還越活越好了,只等著徐孟州稱帝之后,便要做皇后。
原本屬于的位置,現在通通要被盛長樂替代。
而,曾經高高在上、垂簾聽政、獨攬大權的太后,世上最尊貴的人,現在卻淪為一個等待置的階下囚。
因為一個錯誤的決定,走一步,錯一步,一直到無路可退,最后淪落到今日這般凄涼慘淡的田地……
徐瓊華都不明白自己這輩子到底是為了什麼,機關算盡好不容易爬到了巔峰,卻又一點一點將這一些敗壞,把一切拱手送人……
盛長樂進屋,便輕輕抬了抬袖子,吩咐道:“請孩子出去。”
背后的人聽令,便上來將徐瓊華拉開,把懷里抱著的孩子強行奪走。
徐瓊華還想抵抗,“盛長樂,你想干什麼!把麟兒還給我!”
盛長樂端著姿,語氣異常平淡,“我想干什麼,你難道不清楚麼?我們這那筆賬,是不是該算清楚了?”
徐瓊華咬牙切齒,紅著眼瞪著,道:“哀家是太皇太后,你有什麼資格跟哀家算賬!”
盛長樂嗤笑一聲,“現在都改朝換代了,你還當自己是太皇太后呢?”
徐瓊華呼吸急促,道:“只要有哀家在一天,哀家就是太皇太后,麟兒就是皇帝!徐孟州這謀朝篡位的逆賊,只要哀家不寫禪讓詔書,他名不正言不順,不可能得到全天下人認可,逆賊永遠只是逆賊,不配坐這個皇位!”
盛長樂低眉垂眸,了袖口,漫不經心的口氣道:“那恐怕要讓你失了,太后已經代替小皇帝擬下詔書,退位讓賢,將皇位禪讓給鏟除佞、匡扶朝綱的魏王徐孟州,如今大局已定,我本不需要征求你的意見……
Advertisement
一雙眸,幽幽看向徐瓊華,一字一句質問,“你難道還沒認清事實麼?”
徐瓊華心下咯噔一聲,臉頓時煞白。
徐玉珠這個蠢貨!已經同意禪讓皇位了?
徐瓊華已經面難看至極,滿目絕,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倒是盛長樂走進了一些,伏地在徐瓊華耳邊,道:“六郎不愿見你,讓我來告訴你一聲,他念在昔日舊,可以讓你做一個選擇。”
徐瓊華紅著眼,目空,仰頭看著盛長樂,“什麼選擇?”
盛長樂勾一笑,與四目相對,道:“你和你那孽種只能活一個。”
徐瓊華當時就氣得,蹭的一下就站起來,想抓住盛長樂。
不過盛長樂靈巧的往后一躲,沒有被抓到,宮人死死抓著,將摁得坐在了榻上彈不得。
徐瓊華目猩紅,直勾勾瞪著盛長樂,好似恨不得將撕碎片,呼吸越來越急促,好似都能噴出火來。
盛長樂卻只是淡然一笑,“你若是愿意除了你那孽種,六郎尚可放你一條生路,到時候你們依舊是姐弟,可以讓你退居華明宮,留著皇室待遇,榮華富貴,頤養天年。”
說完,盛長樂了袖,便就此轉離去,只留下一句,“你好好考慮一下吧。”
徐瓊華看著離去的背影,已經怒不可遏,只能對著的背影喊道:“盛長樂,我就是做鬼也不會放過你!”
這個選擇,看似是給徐瓊華留一條生路,實則已經將到了死路。
若是當真為了活命放棄兒子的命,這輩子茍且生,被后宮,背負著一的罪惡活著,倒還不如一死了之!
盛長樂從屋里出來的時候,長吁一口氣,頭也不回的走出了垂花門。
徐孟州一直站在外頭等,見抱著孩子出來,才迎了上去。
男人垂目了一眼不哭不鬧的孩子,又看看盛長樂,詢問,“你要留命?”
盛長樂抿一笑,“夫君不愿背負殘害脈至親的罪名,便故意推卸給我,我若是當真殺了,恐怕什麼時候夫君后悔了,又要找我麻煩,我哪里敢?”
徐孟州道:“我當真不是那個意思,就是想讓你有怨報怨,有仇報仇。”
盛長樂別開臉,輕哼了一聲。
兩人正打算離開,還沒有多遠,便聽見背后有喧嘩吵鬧聲音傳來。
回過頭去,便有人匆匆過來稟報,說是太皇太后引火自焚了!
徐孟州和盛長樂匆匆趕過去查看的時候,宮苑已經燃燒起了熊熊烈火,火焰如同一條火一般纏繞著宮苑,在烈的照耀下顯得愈發刺眼奪目,遠遠都能覺到滔天熱浪襲來。
大火燃燒得屋子,徐瓊華沐浴在熾熱火焰之間,烈火一寸一寸在上蔓延,灼燒的痛苦鋪天蓋地襲來,那一瞬間,只讓覺到無窮無盡的悔恨。
若是能重來一次,絕不會再留下這個孩子……
最終,無力的癱倒下去,跟火焰徹底融為一。
宮苑外頭,侍衛進進出出的忙著提水來滅火,可是這麼大的火,徐瓊華定是早就被燒死了。
徐孟州跟盛長樂對視一眼,也只能長長嘆息一聲,盛長樂倒是出乎預料,徐瓊華竟然當真選擇自己死,也要留下這孩子?
懷里的孩子似乎覺到了什麼,眼眸之中倒影出那赤火焰,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哭得是一把鼻涕一把淚的。
盛長樂輕輕拍著他的背安,也無濟于事,漸漸皺起眉,側目看著徐孟州,問道:“那現在,這孩子怎麼置?”
徐孟州道:“給他名義上的母親帶即可。”
這孩子名義上的母親,自然就是徐玉珠了。
徐孟州面毫無波瀾,拉著盛長樂,帶著就此離去,再也沒回頭看一眼,只聞到背后濃煙滾滾蔓延。
一切過往,便猶如這騰空而起的濃煙一般,煙消云散……
一個月以后,當年七月,徐孟州在眾人的擁護下,禪讓正式登基稱帝,改國號為魏,年號啟元,定都鎬京,冊封發妻盛長樂為皇后。
所有有功之人,論功行賞。
猜你喜歡
-
完結13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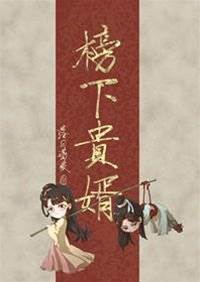
榜下貴婿
預收坑《五師妹》,簡介在本文文案下面。本文文案:江寧府簡家世代經營金飾,是小有名氣的老字號金鋪。簡老爺金銀不愁,欲以商賈之身擠入名流,于是生出替獨女簡明舒招個貴婿的心思來。簡老爺廣撒網,挑中幾位寒門士子悉心栽培、贈金送銀,只待中榜捉婿。陸徜…
46.9萬字8 7390 -
完結791 章
穿越后每天都在努力保胎
比起死回生更扯的是什麼? 是讓死人生娃! 莊錦覺得自己多年信封的科學世界觀完全被顛覆了,每天都徘徊在做個好人這件事上,要不然肚子里那塊肉就會流產,流產了她的屍身就會腐爛,腐爛她就完全嗝屁了。 好在原身有良心給她開了個天眼,方便她薅羊毛,看那位功德加身金光閃閃無比耀眼的小哥,絕對是個十世大善人,完全就是為她保命而存在的! 武都最野最無法無天世子爺:......
141.6萬字8 18598 -
完結183 章

繾綣
昭寧公主沐錦書,韶顏雅容,身姿姣好,是一朵清冷端莊的高嶺之花。 原爲良將之家僅存的小女兒,早年間,皇帝念其年幼,祖上功高,收爲義女,這纔有了公主的封號。 ** 夢裏回到那年深夜,皇兄高燒不止,渾渾噩噩間,他耳鬢廝磨,情意繾綣…… 忽一夢初醒,沐錦書紅着面頰,久久失神。 ** 時隔兩年,於北疆征伐的二皇子領兵而歸。 聽聞此,玉簪不慎劃傷沐錦書的指尖,滲出血珠。 再見時,他眉目深邃,添了幾分青年的硬朗,比起從前膚色黑了許多,也高大許多。 沐錦書面容淡漠如常,道出的一聲二皇兄,聲線尾音卻忍不住微顫。 他曾是最疼愛她的義兄,也是如今最讓她感到陌生的人。
28.2萬字8.18 3505 -
完結329 章

只有春知處
紀雲蘅發現她撿來的小狗瘋了。 見到她不會再搖着尾巴往她腿上蹭不說,給它帶的飯也不吃了,還不讓她摸,就藏在角落裏用一雙大眼睛戒備地看着她。 她只是無意間說了句:聽說皇太孫是個囂張跋扈的主。 就被小狗崽追着咬了大半天。 紀雲蘅氣得把它拴在院子裏的樹下,整夜關在外面,任它怎麼叫都不理,鐵了心地讓它好好反省。 誰知隔日一大早,就有個俊俏的少年爬上了她的牆頭。 ———— 許君赫原本好好的跟着皇爺爺來泠州避暑,結果不知中了什麼邪,每到日落他就會穿到一個叫紀雲蘅的姑娘養的小狗身上。 這小姑娘在紀家爹不疼也沒娘愛,住在一個偏僻小院裏,被人騎在頭上欺負。 這種窩窩囊囊,逆來順受之人,是許君赫生平最討厭的。 可是在後來張燈結綵的廟會上,許君赫來到約定地點,左等右等沒見着人,出去一找,就看到紀雲蘅正給杜員外的嫡子送香囊,他氣得一把奪下,“昨天不是教你幾遍,要把這香囊給我嗎!”
51.4萬字8 326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