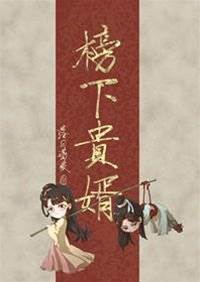《盛世醫香之錦繡涼緣》 第十一章 他們和她們(十一)
玉華公主把自己完的塑造了一個多金的種,對張秀秀一見傾心,已到了難以自拔的程度。
種與花癡只有一線之隔,玉華公主貌無雙,男裝打扮也是俊俏不凡,否則若換個相貌平平的人來表演,只怕會顯得格外油膩。
玉華公主久居深宮,自小看慣了后宮人們的虛偽做作,是以張秀秀這種段位在眼前不過青銅而已。
玉華公主一出場便給張家母帶來了難以抵擋的震撼,俊也就算了,可沒見哪家小廝能一摔就摔出一堆金葉子的。
是以母兩人不但與玉華公主攀談起來,更是同意了相約吃茶的提議。
張父對此卻很不贊同,“秀秀馬上就要嫁給蘇致了,這個時候與外男扯上關系可不妥當。
再者說現實又不是話本子,哪來的那麼多一見鐘,我看像是個騙子!”
張父還是覺得還是求穩的好,與一個不知底細的人相比,蘇致這個狀元郎靠譜得多。
可見識過金葉子和一沓萬兩銀票的張母卻覺得張父實在太沒見過世面了,“這里可是京城,天下腳下,你隨便潑一盆水出去,都能淋到兩個權貴。
Advertisement
蘇致雖是狀元,但家底清貧,如何與那些世家族相比?
今日那位公子相貌出眾,上的料更是華貴無比,瞧著就像大門大戶出來的,做富家夫人難道不比做一個不知前途的太太好?”
張父也被說了心思,想了想便問起了張秀秀的意見,慕艾,早已被那位玉面公子的俊深勾了魂魄,聞言輕輕頷首,咬怯的道:“兒想再多了解他一些。”
蘇致這個狀元郎聽著風,可蘇府除了一個宅院沒有太多的銀錢。
可那位小公子卻不一樣,想想一個仆人口袋里都揣滿金葉子,那該是何等的富貴人家。
見張秀秀如此,張父便也不再反對,只囑咐張秀秀亮眼睛,切勿被小人蒙蔽。
次日,張秀秀如約而至。
世上最了解人的非人莫數,在玉華公主的攻勢下,張秀秀早就將那個不識趣,沉默乏味的狀元郎拋到腦后。
回到酒樓,張秀秀迫不及待的將收到的禮拿出來給父母看,那是一套純金的頭面,造型巧別致,這下就連張父也笑得合不攏。
Advertisement
“你看我說什麼了,那家公子非富即貴,第一次見面就給秀秀送了這麼貴重的禮,怎麼可能是騙子呢!
再者說咱家生意因為裴家徹底黃了,我們上現在一共也就百兩的銀子,人家騙咱們什麼啊!”
張母越發覺得自己的明智,想想日后穿金戴銀的生活,便笑得合不攏。
張父的頭腦還算理智,“秀秀,今日喝茶你可清對方的底細了?”
張秀秀輕輕搖頭,“他只說他姓沈,父親在京中做,其他的沒說什麼。”
張秀秀能覺到對自己是真的十分喜歡,但同時也有所保留。
不過也正是這樣才更讓張秀秀確認對方份一定不同尋常,在徐州時一些紈绔子弟的父親不過就是芝麻大小的,張口閉口卻都是要炫耀一番,反是那些真正的權貴才行事低調。
張父也這般作想,聞言略略思索片刻,開口道:“秀秀,雖然這沈公子條件不錯,但我們還是要給自己留條后路,先別跟蘇致翻臉。
我們也在城各打聽打聽,看看有哪家姓沈的權貴。”
Advertisement
“嗯,爹您放心吧,兒都明白。”張秀秀心中的天平雖然已經傾斜,但也知道要給自己留有后手。
畢竟對沈公子的底細還不清楚,對方雖表現的一片癡心,但遠未到談婚論嫁的地步,自要謹慎為主。
良王府中,玉華公主得意洋洋的與眾人匯報的果,“這種事可太好玩了,皇兄,以后若有這種事我還幫你。”
溫涼抱著小安暖冷冷的掃一眼,糾正道:“與我有何關系?”
玉華公主知道自家皇兄傲的小病,也不理會,仍舊笑容滿面的講著張家人的趣事。
溫皺著眉,橫一句,“這種事我也做得了,本用不到你。”
雖然張秀秀是一個子,可一想到要討好,溫心里就不舒服。
玉華公主一挑眉,“就你?不是我瞧不起你,你除了份好看點,剩下的真是沒有能拿得出手的東西。”
更何況那張家人就像個粘糕似的,就溫那腦子被纏上了絕對甩不掉!
兩人明明都在為對方著想,卻惡狠狠的互瞪彼此。
溫涼瞇了瞇眼,角漫起冷笑,看著似乎有戲……
小安暖睜著一雙清亮的大眼專注的看著自家俊無儔的父親,角也學著父親的樣子勾了勾,疏離清冷的模樣學了個十。
這一幕正被顧錦璃看在眼中,不扶額嘆息。
完了,的兒夢不復存在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3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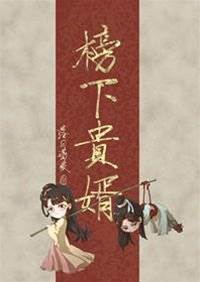
榜下貴婿
預收坑《五師妹》,簡介在本文文案下面。本文文案:江寧府簡家世代經營金飾,是小有名氣的老字號金鋪。簡老爺金銀不愁,欲以商賈之身擠入名流,于是生出替獨女簡明舒招個貴婿的心思來。簡老爺廣撒網,挑中幾位寒門士子悉心栽培、贈金送銀,只待中榜捉婿。陸徜…
46.9萬字8 7391 -
完結791 章
穿越后每天都在努力保胎
比起死回生更扯的是什麼? 是讓死人生娃! 莊錦覺得自己多年信封的科學世界觀完全被顛覆了,每天都徘徊在做個好人這件事上,要不然肚子里那塊肉就會流產,流產了她的屍身就會腐爛,腐爛她就完全嗝屁了。 好在原身有良心給她開了個天眼,方便她薅羊毛,看那位功德加身金光閃閃無比耀眼的小哥,絕對是個十世大善人,完全就是為她保命而存在的! 武都最野最無法無天世子爺:......
141.6萬字8 18598 -
完結183 章

繾綣
昭寧公主沐錦書,韶顏雅容,身姿姣好,是一朵清冷端莊的高嶺之花。 原爲良將之家僅存的小女兒,早年間,皇帝念其年幼,祖上功高,收爲義女,這纔有了公主的封號。 ** 夢裏回到那年深夜,皇兄高燒不止,渾渾噩噩間,他耳鬢廝磨,情意繾綣…… 忽一夢初醒,沐錦書紅着面頰,久久失神。 ** 時隔兩年,於北疆征伐的二皇子領兵而歸。 聽聞此,玉簪不慎劃傷沐錦書的指尖,滲出血珠。 再見時,他眉目深邃,添了幾分青年的硬朗,比起從前膚色黑了許多,也高大許多。 沐錦書面容淡漠如常,道出的一聲二皇兄,聲線尾音卻忍不住微顫。 他曾是最疼愛她的義兄,也是如今最讓她感到陌生的人。
28.2萬字8.18 3505 -
完結329 章

只有春知處
紀雲蘅發現她撿來的小狗瘋了。 見到她不會再搖着尾巴往她腿上蹭不說,給它帶的飯也不吃了,還不讓她摸,就藏在角落裏用一雙大眼睛戒備地看着她。 她只是無意間說了句:聽說皇太孫是個囂張跋扈的主。 就被小狗崽追着咬了大半天。 紀雲蘅氣得把它拴在院子裏的樹下,整夜關在外面,任它怎麼叫都不理,鐵了心地讓它好好反省。 誰知隔日一大早,就有個俊俏的少年爬上了她的牆頭。 ———— 許君赫原本好好的跟着皇爺爺來泠州避暑,結果不知中了什麼邪,每到日落他就會穿到一個叫紀雲蘅的姑娘養的小狗身上。 這小姑娘在紀家爹不疼也沒娘愛,住在一個偏僻小院裏,被人騎在頭上欺負。 這種窩窩囊囊,逆來順受之人,是許君赫生平最討厭的。 可是在後來張燈結綵的廟會上,許君赫來到約定地點,左等右等沒見着人,出去一找,就看到紀雲蘅正給杜員外的嫡子送香囊,他氣得一把奪下,“昨天不是教你幾遍,要把這香囊給我嗎!”
51.4萬字8 326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